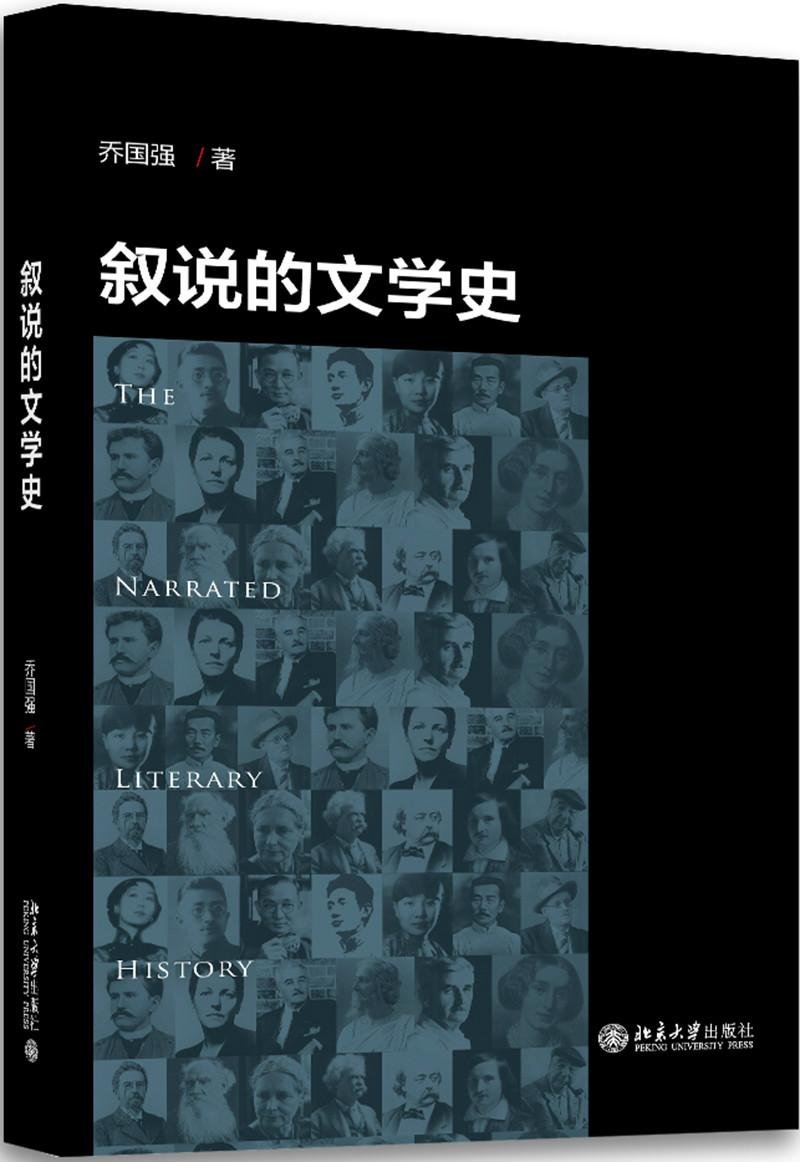
《叙说的文学史》一书运用叙述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来讨论文学史的本质性问题及其属性。该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梳理已有的学术成果,对中外的文学史观,及文学史写作进行了系统全面地讨论;第二章、第三章运用叙述学的基本概念讨论文学史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及文学史中的“秩序”问题;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理论高度讨论了文学史的表现叙述、虚构性、三重世界及其叙事模式等重要问题。最后一章作为结论高度凝练地总结了该书的主要观点。
文学史叙述
——评乔国强《叙说的文学史》
方小莉
《叙说的文学史》一书运用叙述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来讨论文学史的本质性问题及其属性。该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梳理已有的学术成果,对中外的文学史观,及文学史写作进行了系统全面地讨论;第二章、第三章运用叙述学的基本概念讨论文学史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及文学史中的“秩序”问题;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理论高度讨论了文学史的表现叙述、虚构性、三重世界及其叙事模式等重要问题。最后一章作为结论高度凝练地总结了该书的主要观点。
文学史研究由来已久,中外学界皆如是。然而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比较偏向研究文学思想、具体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及其地位等,也就是说更为关注文学史讲了“什么内容”,而甚少关注文学史的形式问题,即文学史“怎样”讲述。虽说现有的文学史研究也对文学史的本质问题进行过探讨,但是却“忽略了文学史的内部组成因素及对这些组成因素在叙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功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所蕴含的意蕴”(25)。《叙说的文学史》在梳理中西方文学史观的基础上,借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将文学史作为一种叙述文本,通过对其叙事的讨论,来看清文学史叙述的本质问题及其属性和特点。(6)
对文学史的讨论首先要意识到 “文学史毕竟还是一种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文学史撇开叙事这一层面是不完整的和不彻底的。”(91)那么文学史研究便不能只从观念出发,而是应该进一步探讨文学史写作的内部构架、文学史叙述的性质与特点。承认文学史是一种叙述文本,那么它便具有叙述文本的基本构成和特点,《叙说的文学史》首先讨论了文学叙述的叙述主体,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时空、伦理及“秩序”问题。
传统对文学史的讨论是将“史”视作一种纪实性叙述,因此将作者等同于叙述者,从而文学史的体裁决定了其叙述的可靠性问题不容置疑,因为作者与叙述者的价值观之间没有距离。《叙说的文学史》承认“文学史家与文学史叙述者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然而由于一方面 “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中使用的是第三人称,而并非是表明他、她自己身份的第一人称,所以不能把二者截然等同起来;二是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学史叙事其实都是一种集体性的叙事。”(95)在此基础上,乔国强教授提出文学史的三重述体概念:
述体1:身体——文学史家本人的身体存在
述体2:表达身体的人或产生意义的人——文学史家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叙述者
述体3:文本因素——文学史文本或被印刷、被书写之物。(98)
文学史家本人是有血有肉的作者(身体),身体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虽然不说话,却影响或决定文学史家对史学文本的建构。他将表达身体的文学史家,即执行作者,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叙述者,同时“将叙述者所代言的 ‘文本因素’ 吸收进来,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框架结构。这一 “三元论”不仅更为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文学史的叙述主体问题,同时也使文学史的可靠性问题遭到质疑,从而丰富了对文学史叙述的讨论。
任何叙述都是一种媒介化,也即是说必然是有选择的再现,那么则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再现允许优先选择某些材料而摒弃其它的”(科布利:4),哪怕是历史记录也是“符号构成的话语实体,那么它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再现便完全是选择性的。”(科布利:21)文学史也是如此,文学史的作者或读者在解释真实发生的事件过程或因果律时通过叙述化,主观赋予叙述文本叙述性,从而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文本中总存在“对一些优先事件的再现”(科布利:21)。《叙说的文学史》一书将文学史的这种叙述再现称作“表现叙述”。所谓的“表现叙述”是“一种以文字为媒介、以文本为形式,用“叙述”的方法来表现并揭示所谓历史事实及其内涵的表现模式。”乔国强教授在这里将“表现”与“叙述”两个词合而为一,“用来共同揭示文学史写作的本质、形式、方法以及目的”(192)《叙说的文学史》一书提出文学史“叙述的方法和目的是“表现”,即尽可能地客观叙说文学历史的史实,” 这体现出文学史的纪实性特征。但同时本书还提出“ ‘表现’本质是重构,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表现”的方式是 ‘叙述’”,具有多元的属性”。(173)表现的本质是重构,则说明文学史是有选择的再现,再现的形式决定了再现的结果;表现的方式是叙述,那么不同的叙述者,在不同的语境下,由于视角、时空、叙述方式,价值观等的不同,则会产生多元的叙述,从而也使文学史不是稳定不变的史料堆积,而是被叙述化为不同的“他的故事”。如同所有历史写作一样,文学史写作以文字为媒介,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再现。文学史“表现叙述”要表现的既是有明显因果关系的共时性文学人物、作品、事件等,也要表现这种没有明显因果关系的历时性文学人物、作品、事件等,让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基本的叙述时空构架,并由此而形成一种历史标志。”(192)
《叙说的文学史》认为文学史作为一种叙述,其虚构问题不可避免。“文学史的虚构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凸现:一个是文学史叙事的性质,包括其构建与意义产生的方式;另一个就是对作家、作品以及其它文学事件入史的遴选标准和评价问题。”(221)从上面的两点可以看出文学的虚构性与其叙述性有密切关系。正如前面所说,文学史作为一种叙述,是一种媒介化的再现,那么就具有高度的选择性。首先从指称性来看,即文学史是否指称现实,文学史的撰写是文学史家根据自己的文学史观来遴选历史事件、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等,再以自己叙述方式书写成书。事实上,“无论是按照哪种史学观点来撰写文学史,都是不可能把所谓的真实的、全貌的文学历史展示出来的,都是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虚构性。(224)同时,文学史 “处理的也并非都是真实的史料,而在处理时会打上文学史家的主观性,这些主观性也是文学史虚构性的表现”(242)从文学史的 “建构性”来看,“叙事是可以改变事实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叙事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事实模式。”(219)也就是说叙述文学史的基本策略或模式等形式问题决定了文学史书写的结果。当然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也参与了文学史的建构。文学史家“将一些相关或不相关的人物或事件放在一起,从而构建起一种意义组合。不同的文学史作家会有各自不同的构建方式,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组合。”(224)因此文学史的“虚构性”使文学史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正如奥特利(Keith Oately)所说,“虚构”并非是不真实,而是“制造”。小说和诗歌是关于可能发生什么(7)。同理,文学史作为一种叙述,也是文学史家以各自不同的建构方式,构建起了文学史文本世界的各种可能性,通过统一的底本书写出各个不同的述本。
值得注意的是,乔国强教授明确指出文学史的虚构性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具有三重意义的虚构性:第一种虚构主要是针对研究对象而言,这种虚构不仅包括人物塑造和故事构建,而且还包括作者在叙说这些故事时所采用叙述策略等。第二种虚构是从文学史的本体上予以考察,指出文学史写作如同其他写作一样,并非是对文学史全貌的照录,而是有着写作原则和编排体例要求的。第三种虚构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文化与社会语境层面上来予以考察,指出文学史写作与塑造或影响文学史作者的文化传统、社会实现、时代精神、审查制度等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249-250)
《叙说的文学史》既全面又创造性地探讨了文学史叙述,各章节所讨论的问题分类清晰、相互不重叠又覆盖全域,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学史叙述理论研究体系。通过对文学史形式的探讨,促使读者看到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架构,文学史的根本特征和属性,也承认文学史的虚构性,从而让文学史“能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至少能让人们意识到那份难以言传的真实。”(234)
参考书目:
乔国强:《叙说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保罗·科布利著:《叙述》,方小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
Oatley, Keith. Such Stuff as Dreams: The Psychology of Fi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