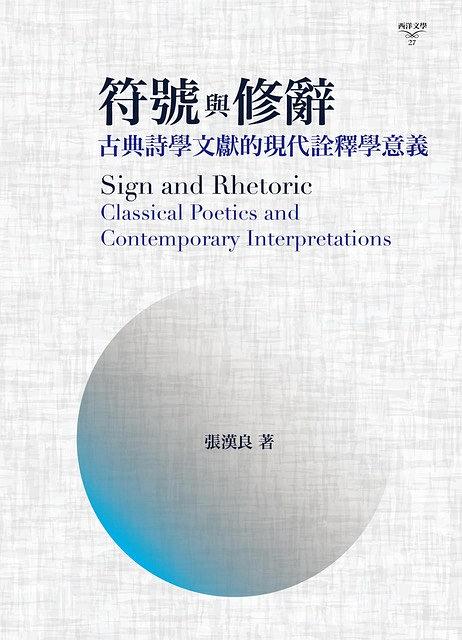
张汉良教授的《符号与修辞: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于2018年12月出版,这部近五百页的厚重之作是在张先生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荣休之后起笔始撰,历时六年完成,然而书中每一个章节都由作者数十载的沉潜思索提炼而来。这部著作择取西方古典时代先哲著述中与诗学相关的课题,钩陈它们与当代文艺理论的源流关系。
一部“符号诠释学”视角的元诗学
——读《符号与修辞: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
唐珂
作者简介:唐珂,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诗学。本文得到2018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西方‘诗辩’的理论范式考辨与语用文体研究”(2018EWY007)资助。电子邮箱:kirstiet@126.com
张汉良教授的《符号与修辞: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于2018年12月出版,这部近五百页的厚重之作是在张先生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荣休之后起笔始撰,历时六年完成,然而书中每一个章节都由作者数十载的沉潜思索提炼而来。这部著作择取西方古典时代先哲著述中与诗学相关的课题,钩陈它们与当代文艺理论的源流关系。“符号”与“修辞”这两个核心术语,既是该书的对象文本的线索枢纽,亦是其方法论视野。这部著作从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考察了多个理论课题的互动与争鸣——诗艺与诗辩传统,关于隐喻的论辩,记忆与叙述、诠释的关系,古典诗学与生物学范式之间的因缘等等,它将符号学、语言学分析与语文学、科学史研究有机结合,于古典学与比较文学而言俱是一种别出机杼的探索。
所谓识古方知今,“学术的前瞻性往往吊诡地建立在历史回顾上。”(张汉良 2018:2)古典学与比较文学素来渊源深厚。古典学本就具有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视野,当代古典学者亦注重新研究方法的运用;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弄潮儿们,泰半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学养。古典学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已愈来愈被比较文学学者所重视。《符号与修辞》所研讨的对象文本,有西方文学批评史中的经典,更有大量鲜见于文学批评史著述或教材的哲学篇章——柏拉图《克拉底鲁篇》、《梅诺篇》,亚里斯多德《范畴篇》、《论灵魂》,以及斯多亚学派和怀疑论者的著述;所涉文本除大量古希腊文、拉丁文文献外,亦借鉴德文、法文、捷克文、英文文献;所涉猎的主要学科有逻辑学、修辞学、生物学、神经科学,这一切考掘与检视的最终落脚点是诗学。
然而这本书并非一部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五个互相交叉的主题——摹拟与创作、动物与灵魂、记忆与书写、符号与逻辑、修辞与话语构成一个诠释的网络统摄全书二十章,让这一互动网络中多种话语机制的不同动机得到解释和定位,最终凝聚为标题的两个核心关键词“符号”与“修辞”。如作者在序言中所道,“既不奢求穷尽材料,更非仿史书或概论的宏观笔法。”(1)张先生在研究摹拟、灵魂、书写、符号等概念的古今含义时,既注重厘清它们彼此的“基因关系”,更着力探析它们的“类型学对应关系”[1],一如张先生的故友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称自己的《象征理论》(Théories du symbole)为虚构的历史,是作者有意择取的管中窥豹,又如张先生的另一知交杜勒谢(Lubomír Dolezel)的《西方诗学》(Occidental Poetics)对欧美诗学诸家展开建模式研究,重构了大半部西方诗学史,《符号与修辞》同样采取的是以问题为导向、对范式进行梳理的系谱性研究。正如作者所言,“当代学者‘共时性’的对话,实肇始于他们和希腊先哲的‘历时性’对话;或者——更‘根本’地说——所谓历时性,也无非是共时性的产物。”(4)《符号与修辞》的方法论基底是索绪尔现代语言学革命所开创的共时性研究模型,该书亦是一部以诗学为对象语言的元诗学(metapoetics)。
“符号”与“修辞”这两个词在比较文学界人人皆知,却鲜为并视。符号的概念自古典时代已有,但它在古典诗学、哲学、人文教育中被探究的方式尚待发掘。百余年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与美国逻辑学家皮尔士各自独立地为符号学作为全新学科的创立奠定理论基石。索绪尔把建立在连续史观之上的语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史前史,而将共时语言学作为开拓的土壤。索绪尔提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一切研究成果都从这个重要的事实生成其表意机制(signification)。”(Saussure 35)法国学者本维尼斯特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基础上开辟了“第二代的符号学”——话语符号学,推动了1970年代语用学研究的热潮,而修辞学自肇兴之初便是研究“语用”的学问。修辞学在古典时代后期成为一门学科,被列入中世纪自由七艺,论辩术与辞格学成为其两大分支,它曾经衰落又数度复兴与革新。修辞本是旨在实现某种语用目的的话语交际技艺,它与“”(poetics的词源)密不可分。如今为不同学科所重视的修辞学,在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时代,只被视为“形而下者”、雕虫之技,柏拉图从政教和真理的视域下贬斥文艺,然而他的对话录本是一篇篇多声部的哲学戏剧,以“高贵的谎言”之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贺拉斯的时代,新修辞派的兴起促使人们自觉地对作品精雕细琢,重视创作的技艺。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为诗辩护的同时也是在为修辞辩护。20世纪,贝荷曼(Chaïm Perelman)的“新修辞学”与列日学派(Groupe μ)的“一般修辞学”在承接古典传统的同时让修辞学与诠释学、符号学、语用学等学科密切互动。罗兰·巴特将内涵符号学视为未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内涵符征(connotator)的形式[2]即是修辞。(Barthes 90-91)后现代之所谓“文学胜利”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修辞的重释和复兴实现的。保罗·德·曼宣称修辞是语言最典型的范式,是“语言最真实的本性”(de Man 1979: 105)。广义的文学之体可以指“任何或隐或显地对自身修辞模式的表征(signify)以及对自身的误读的预示(prefigure)”,“这种误读与其修辞的本性或者说‘修辞性’紧密相关。”(de Man 1971: 136)德·曼使用的“signify”是符号学的术语。巴特的《爱的言谈——片断集》以意识流般的自述试图挣脱表意秩序的牢笼,修辞的语用目的含混不清,或者说修辞本身成为了主角,每一个反思性的小标题则与主体的呢喃构成反讽,如同在否定了旧的神话学之后营建了一种新神话学。这两位解构主义旗手恰与结构主义符号学渊源深厚。
“符号”与“修辞”这两个核心术语,既是《符号与修辞》的对象文本的线索枢纽,亦是其方法论视野。该书的副标题是“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不免让业内人有所疑惑。诠释学与符号学这两个在20世纪学界鼎鼎有名的术语,在上个世纪的发展路径南辕北辙。诠释学由中世纪释经学发展而来,18世纪由施莱尔马赫系统化为一门方法论,到了20世纪,伽达默尔以“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理论将诠释学提升至本体论的哲学高度。作为一门探讨“理解”或“领悟”(Verstehen)的学问,诠释学的旨趣往往是对文本深层含义追根溯源。符号学的研究思路恰恰是自下而上的,它由最小的意义表征单位入手,探究表意系统逐层建模的机理,符号学认为读者的诠释话语是对所接收的信息的解码与再度编码,必定是读者的视野、知识经由语言中介的产物。作为语用行为的诠释,必绕不过符号与修辞的问题。《符号与修辞》多个章节探讨的是哲人与诗辩者的古今对话,然而“对话”这个说法实为一个隐喻——“从个人‘书写’变成两人‘对话’的过程那么自然顺畅吗?中间没有质变吗?某一历史场景的‘言谈’(言谈1)变成后来某人的‘书写’(书写1),被更后来的读者阅读的‘书写’(书写2)又被还原为再建构‘言谈’(言谈2),难道这不是德希达亟欲解构的‘理言’(逻格斯)中心论吗?回到语言系统,我们发现言谈与书写的转码需要透过一系列的符号演绎才能启明。”(张汉良 2018:3)因此,文本的释义最终需诉诸符号学的方法以考量。
这部著作的一重深意,正是在方法论上对诠释学与符号学的汇通。尽管书中多次以批判性的眼光引用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说法,作者在序中特地对副标题中的“诠释学”作如下解释:“此处‘诠释学’一词为普通名词,极广义的用法;严格说来,它指文本‘诠释’与意义建构现象,而非特定的某家某派的诠释学。”(2)张先生曾在《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一文中,假罗曼·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的语言交际模型讨论修辞学何以介入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雅可布逊的传播模式可以继续扩大涉及语言使用者的行为,并使得涵盖修辞学研究的符号学和诠释学沟通。”(张汉良 2011: 30)施莱尔马赫曾指出,诠释学不仅包括“语言”系统与个别“言语”的表意过程,也包括言语发送者和接收者透过语言媒介所实践的交流行为。修辞学与诠释学分居语用学的两端,皆需话语场景中人的编码与解码工程。对文本的诠释无法脱离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这就是为何施莱尔马赫特别强调对话(Reden)与理解(Verstehen)的关系;张先生认为颇为遗憾的是,当今的部分读者忽视了现代诠释学自肇兴之初便为施莱尔马赫所重视的“语言文本物质成分”,“事实上如果没有发送者的语言建码行为以及接受者的语言译码行为,也根本就不会有诠释学。”(张汉良 2018:7)阅读-释义同样是修辞活动,因为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伪)记述语言与施为语言的结构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旨在彰显语言符号的表意机制与交际方式的符号学,与诠释学是为一体共生,这正是为何张先生在“符号与修辞”的主标题下将副标题命名为“古典诗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学意义”。
如蒂尼亚诺夫(Yury Tynyanov)所言,建构一种文学的发生史是不可能的,但书写一部文学系统的历史却完全可行。这一说法也适于对古典诗学的研究。《符号与修辞》的行文脉络并未依照线性历史进程的顺序展开,而是以主题为定位。多章的时间节点有所交叉,作者尤其关注不同阶段诗学话语的内在关联和深层契合。该书第一篇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3]起笔,考察《诗学》在亚里斯多德学术系统中的定位,澄清《诗学》的生命科学基础,以摹仿论串起柏拉图《智者篇》与贺拉斯《诗艺》之于《诗学》的启发和传承,还原这一诗学命题的历史脉络;张先生将《诗学》视为“诗辩”文类的鼻祖,钩沉出后世锡德尼、雪莱、奥登的诗辩话语,尤其是魏尔伦与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隐喻式的摹拟行为。张先生继而由《诗学》对“灵魂”的隐喻谈起,解析灵魂的两种能力“忆”和“记”,再以“记忆”为核心,串起对《斐德诺篇》、《蒂迈欧篇》、《会饮篇》、《伊昂篇》的细读,彰显“语义世界之内的斐德诺和语用世界内的书写主体柏拉图的镜像摹拟关系”(126),界说语言为记忆和欲望建码的功能;作者对德里达《柏拉图的药》中一个个关键词的双关义、隐喻义、语用义抽丝剥茧,且评析德国耶拿学派如何挪用《会饮篇》以申言浪漫主义广义的“文化记忆”说,是为近年热门的文化记忆理论溯其源流。在“符号与逻辑”版块,张先生细致考掘了为当代古典学者所忽视的柏拉图《克拉底鲁篇》(台译《克拉提娄斯篇》)对言语和书写之关系的论断,且就《克拉底鲁篇》中的名实之辩与对“身体”和“符号”的探讨这一系列问题,将这一古典文本与索绪尔的名著及手稿对观,辅论热奈特《摹拟学:航向克拉底鲁》(Mimologiques: Voyage en Cratylie)中的“克拉底鲁主义”和198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与文学界的“象似主义”潮流。在最后一个版块“修辞与话语”中,张先生首先借雅可布逊的语用模式检视修辞学对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贡献,继而分析柏拉图《梅诺篇》和圣奥古斯丁《师说》以对话结构传达的共同悖论,解读罗兰·巴特标举“中性”话语的新修辞学试验与德里达《白色神话》对亚里斯多德《诗学》隐喻观的解构,张先生从语言学科史出发,重新检讨福柯的“话语”概念,且引柏拉图多篇文献章句作为对福柯的“回应”和申辩。有趣的是,全书自亚里斯多德的“诗辩”始,以作者代亚氏导师亦是其反驳对象柏拉图申辩为结;作者将数个人人皆知却语焉不详的“晦涩”概念贯穿始终,对其抽丝剥茧;与先辈对话的作者在时空中几度穿梭,对话的线索主题却条理分明,而支撑每一个章节架构的都是深厚的语文学养与辨章学术的严谨考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跨学科研究可谓比较文学各方向中难度最大的一种,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方兴未艾,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古典学研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阵地中尚待垦拓的一块。《符号与修辞》成功地实践了符号学、语言学与语文学、科学史的跨界汇通,最终落脚于诗学。这部别出机杼的古典学著作亦是中国学者为国际古典学研究所贡献的一部掷地有声的传世之作。在笔者写此书评之时,已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之龄的张先生又兴致盎然地投入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新课题。前辈学者如此孜孜不辍,吾辈晚生虽难望项,亦知须锐意勤勉。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Barthes, Roland.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s.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8.
De Man, Paul.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De Man, Paul.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Hjelmslev, Louis.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 Francis J. Whitfie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 Payot, 1997.
张汉良:“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上)——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当代修辞学》1(2011):27-37。
[Zhang, Hanliang. “Rhetoric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 A Survey of Modern Methodology and a Case Study of Ancient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xiu ci xue yu bi jiao wen xue yan jiu (shang) yi ge xian dai fang fa lun de kao cha yu gu dai zhe xue dui hua de shi li fen xi). Contemporary Rhetoric 1 (2011): 27-37.]
张汉良:“透过几个图表反思‘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2014):159-170。
[Zhang, Hanliang. “Rethinking ‘Studies of Literary Relations’ Through Several Diagrams” (tou guo ji ge tu biao fan si wen xue guan xi yan jiu).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2014): 159-170.]
[1] 这对术语来自捷克比较文学家杜瑞辛(Dionýz Ďurišin),参阅Ďurišin, Dionýz. Les courants littéraires dans le système de l’étude comparée des littératures / / ACTES du V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Belgrade 1967. Ed. Nikola Banašvič. Amsterdam: Swets & Zeitlinger, 1969. vol. 1. 转引自张汉良:《透过几个图表反思“文学关系研究”》,见于《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166页。
[2] 此指叶姆斯列夫意义上的形式(form),与实质(substance)相对。参阅Hjelmslev, Louis.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 Francis J. Whitfie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3] 在古典诗学语境下,“poetry”是文艺创作的总称,涵盖悲剧、史诗等各种文类。因此张先生把《诗学》亦译为《创作论》。亚里斯多德为其摹仿论所展开的辩护是为革新柏拉图的摹仿论,文艺创作的摹仿能跃居知识(επιστήμη)和技艺(τέχνη)的行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根据普遍的理念被界定和分类,能够揭示普遍的智慧——它的内在结构和运作过程具有知识的特征。通过对创作(尤其是悲剧)的系统化和科学化,亚里斯多德实现了对文艺的正名,悲剧正是这种“创制科学”(ποιητικῆς)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