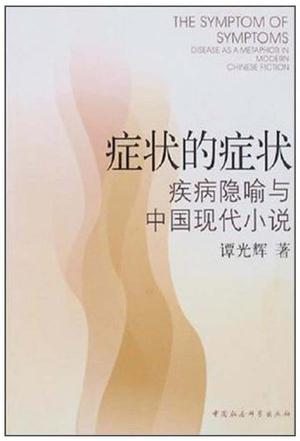
我小时候是个病秧儿:五六十年代,少年期肺结核依然肆虐中国,但那个时期,青少年理应健康如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个少年竟然患肺结核,哪怕肺结核病患者当时很多,都是不应当的事,理亏的事。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学校休学。
症状的症状
我小时候是个病秧儿:五六十年代,少年期肺结核依然肆虐中国,但那个时期,青少年理应健康如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个少年竟然患肺结核,哪怕肺结核病患者当时很多,都是不应当的事,理亏的事。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学校休学。
读到谭光辉的书《症状的症状》,我回想自己的病史。谭光辉讨论的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疾病主题,而是这个主题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为主题的原因。这就是此书的核心论题:病到底是患出来的,还是讲出来的?科学界对讲述极其怀疑,因为讲述把细节串成一个有时间顺序因果链接的故事,就必然带着道义目的论,科学的客观性却不允许有目的论。医学是科学,应当拒绝讲述,病痛也是真切的感受,但是医生听病人讲述,学校的老师听医生讲述,家长听老师讲述,我听父母讲述,最后的休学,就成了这一连串讲述的结果。原先是一堆症状,一叠病检材料,实实在在的科学证据,经过一连串的讲述,毫无虚构地讲述真相,其结果是未曾预料到的:被讲述的对象原是病的症状,最后讨论的却是对我的处理:被讲述的对象推到意义指涉圈的背景中:在语言对前因后果的讲述中,病本身变成了语言的构筑。这时医生反而“保护”头疼脑热之类症状,不愿意匆匆对症治疗,他要留下症状为讲述提供“事实根据”,至少,他要仔细保留在病史里。
我不能说医学认为症状比疾病重要,对我的处理,也是为社会认同的。的确,生病经历不是小说的虚构,但是一旦牵涉到社会的态度时,文学的虚构讲述,与医院学校的“客观”讲述,恐怕区别不大:一旦需要对疾病进行讲述,就需要社会的共识,需要人们的信念。讲述有理了,病也就存在了,有了意义在场的充实性,疾病就成为疾病。
谭光辉的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疾病的意义在场,告诉我们疾病是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讲述出来的。不仅如此,此书还告诉我们现代中国每一阶段,对疾病的讲述,不仅质上不同,量上也不相同。他的书,谈的是症状的症状,也就是对中国文学的病症描写做做“症状阅读”。此种阅读阐释方法,在中国学界,已经有人做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做到如此大的规模,贯穿整部文学史。历史一旦贯穿,就不是让个别作品变成詹明信说的民族讽喻,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喻。
如果批评者把文本看成病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批评者怎么会有这个洞察力,看到讲述背后的真相?看到症状的症状?这个论题的难点就在这里。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我们要解释什么真相?这正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讨论的不是小说中疾病主题背后的真相,而是疾病讲述本身的真相-----他雄辩地证明了,讲述背后找不到真相,讲述本身却有真相:每当中国社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什么,“中国人病了”的讲述就处处出现,“东亚病夫”就成为中国人激烈的自我批判的武器;每当中国社会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一门心思干劲十足,中国人就没有病了,中国文学也就不写疾病。所以,中国社会有病时,恰恰文学认为自己无病时;而当文学尽在说中国人病之时,中国社会反而具有反思能力。
作者把疾病讲述看成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产物,而不是笼而统之的“中国文化”产物,这样他就超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关于疾病讲述的真相,就不在讲述疾病的文学之中,而在文字之外;不在小说讲出来的情节里面,而在小说未讲,不能讲,不可讲的地方。作者着力分析的,不是讲述话语的意义本身,而是作家这些“文化中人”的意识,如何让他们用每个人自以为特别的方式做病症讲述。因此谭光辉做的,不是刘鹗那样诊病开方,也不是鲁迅那样只诊病不开方,他是在拷问这些医案,这些病史,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时,唯一让我们明白的疾病讲述真相,就是真相本身的隐身病症。小说讲述的,是真相的反面,或者说,一旦被小说讲述,真相就不在场了。
那么谭光辉本人如何能逃脱这个讲述悖论呢?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讲述说得头头是道时,我们如何能肯定他没有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疾病符号文本化呢?是的,这的确是一个怪圈。要跳出这个怪圈,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作自我反省:不断提醒自己,无论哪种讲述本身,终究是一种目的论行为,容易在力求自圆其说的努力时,构筑另一个讲述迷思。我认为谭光辉的书中,表现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试看他讨论所谓疾病与变态的这段精彩论述:“反对变态的批评是权力话语的奴隶,容许变态的批评是自我的主人,前者是批评的变态,后者才是批评的常态”。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自己思想方式的审慎,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文化批评家对主体能力有限边界的自觉。应当说,这本书对符号文本的性质理解如此透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很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