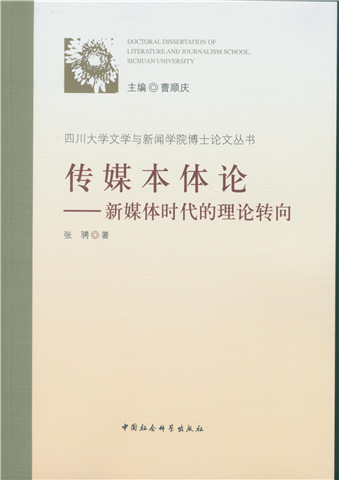作者:
陆正兰 来源:
浏览量:3841 2016-10-04 14:58:10
新媒体与新的共同主体性
——评张骋的《传媒本体论——新媒体时代的理论转向》
陆正兰
张骋 《传媒本体论——新媒体时代的理论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在当代理论家中,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代表哈贝马斯,对共同主体性的建立最为热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行为相互理解,并分享共同主体性。他提出:“语言行动不只是服务于说明(或假定)各种情况与事件,言语者以此同客观世界中某种东西发生关联。语言行动同时服务于建立(或更新)个人关系”[①]。
而此刻,张骋这本《传媒本体论》讨论的虽然不是语言行动问题,而是新媒体和人的主体间性,及共同主体性问题,精神上与哈贝马斯相同。“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传媒化生存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与传媒联系在一起,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被传媒所决定。”想必读到这样的描述,身处当代文化中的我们,都会产生共鸣。
20世纪,新媒体迅猛发展,使人类进程突然加速,许多原先只存在于人类想象中的世界,变得触手可及,传媒技术的后果甚至超过了麦克卢汉的诸多预言。当代的“传媒转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一场由技术引导文化,再由文化反作用于传媒,改变人类思维,改变世界的深刻而全面的革命。这样的一场媒介变革,正改变着人类命运,改变着人类原先与自我,他人,自然、社会的关系,这个现实背景,让张骋带有哲学思考的论著《传媒本体论》,更显理论和实际意义。
作者这样说,“本体论是关于终极存在以及人与世界总体性关系的学说”,讨论传媒的本体论,也就是 “从主体间性关系中去考察传媒,将传媒看成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中的非中性的本体或主体,人和世界都存在传媒之中,传媒决定任何世界的意义”(18页)这样,新媒介相对于传统的中性工具意义来说,就成了主体间性关系中的主体,甚至具备了哲学向度上的意义,“媒介是存在之家”。
这本书志存高远,力求解决当今传媒时代面临的形而上问题。上篇讨论“传媒本体论何以可能”,从技术哲学,传媒哲学和传媒文化三个层面,论述传媒本体论的立足点和理论依据;下篇探究“传媒本体论如何可能”,辨析的是新媒体和现代主义哲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化及各种文艺新形态的关系。这样,“传媒转向”的论述就由文化传媒化和传媒文化化,两各方面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此书论述的焦点集中于传播,但此书论述学术视野极其广阔,打破了“新闻无学”陈旧观点。作者每个理论点,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分析透彻。比如,在论述传媒本体论的立足起源时,作者深刻剖析它与“技术哲学”的关系,详细梳理了技术哲学的兴起和发展脉络,对古代、近代和现代哲学家对技术的观点和态度逐一分析。谈到近代,作者将其分成两派,以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洛克代表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以及以卢梭、康德、赫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并对马克思“技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与解放”进行了辩证的剖析。在分析现代哲学家对技术的看法时,作者总结海德格尔现象学视野中的技术,写道“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展现方式”,不仅有自己的理解,还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一脉相承。
在探讨新媒体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时,作者对新媒体的后现代主义“中心的消解”“结构的颠覆”“基础的坍塌”以及“理性的陨落”等文化表征,都有准确的辨析。比如,在论述新媒体对基础的解构时提出,赛博空间建立的实际是一个虚拟实在空间。“在空间中活动的人都是现实的人,在空间中发生的事情都有现实的后果。”(131-132页)“它是在意义上存在,而不是在事实上存在的事实或实体”(133页)。这样,人在以赛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中的存在,就是一种意义的存在。就犹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是来源于我们对意义的关切。赛博空间让人类获得了新的意义及其存在方式。
同样,在论述新媒体与各种新的文艺形态的关系时,比如网络文学、微电影、网络游戏等,作者的观点犀利而精辟,将他们总结为这些都不是“人使用传媒”,而是“传媒使用人”(201页)的新形态。它们就如同鲍德里亚的一些术语“仿真、超真实、内爆”一样,既是后现代文化的表征,也是传媒技术的展演,是与新传媒与后现代文化相匹配的事物的一体二面,在人类的进程中,继续与人类共享共同主体性。
今天当我们在探讨传媒的本体论问题时,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改写并推进哈贝马斯的观点,将“语言”改为“新媒体”,可以依然沿着哈贝马斯称为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的路径前行,实现一种理想的媒介和人类共享的主体性:“通过这种内部活动,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相互决定他们个人的行动计划。因此可以无保留地追求他们非语言活动目的。”[②]不同的是,这种社会理想境界的蓝图,推动力不再是语言,而是在21世纪甚至未来,走得更远的新媒体和人类自身。
这样一本著作,或许有某些理想主义色彩,但传播学如果一直停留在作为工具,提供技术的浅层次上,就无法穿透我们面临的时代,更不用说我们正在快速进入的未来。我们时代急需对传播的形而上思考,作为一位青年教师,张骋面对时代的挑战当仁不让,他的观点值得我们好好倾听,仔细思辨。这是一本传播界应该细读的好书,它让传播学从一味“接地气”的爬行,展翅飞翔了起来。
[①] Jue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p.52.
[②]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