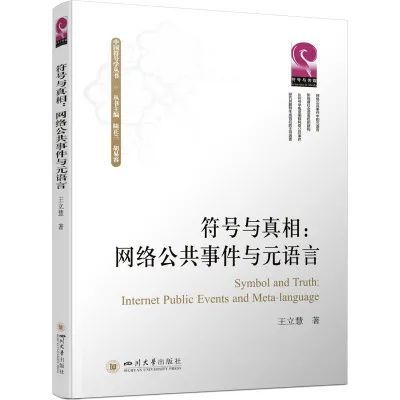
社会不断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相应的传播科技、媒介制度、传播组织与信息生产能力。而同样的,每个时代也都会出现新的问题与答案。对中国来说,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的社会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意见表达也愈来愈公开化与网络化。与之相对,国内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亦大量出现,然而这些研究往往立足网络公共事件的过程、理论研究与应对措施,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研究上却出现了罕有的空白。针对这一畛域,作者王立慧创新性地从符号学与传播学整合的方向入手,围绕“意义建构”的核心议题,在符号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完成了该著作的撰写。
魏瀚扬评王立慧著《符号与真相:网络公共事件与元语言》
魏瀚扬
社会不断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相应的传播科技、媒介制度、传播组织与信息生产能力。而同样的,每个时代也都会出现新的问题与答案。对中国来说,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的社会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意见表达也愈来愈公开化与网络化。与之相对,国内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亦大量出现,然而这些研究往往立足网络公共事件的过程、理论研究与应对措施,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研究上却出现了罕有的空白。针对这一畛域,作者王立慧创新性地从符号学与传播学整合的方向入手,围绕“意义建构”的核心议题,在符号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完成了该著作的撰写。
除导论外,本书共分为六章,从公共事件的定义出发,进而讨论了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问题、分析此类事件的符号学路径、元语言的争夺、离散与与真相相关的联系等。以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元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本书从更高的层次与更深入的角度剖析了网络公共事件解释中涉及“有关意义和元语言控制的符号学问题”。在研究范式上,除传统的、西方视角的传播学理论外,本书还揆诸实际、结合当下国内的网络公共事件进行符号学元语言与其内部权力表达的考察,为网络公共事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与更本土化的深入解读。
一、回溯与定义
在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进行深入探讨前,明确公共事件的历史沿革与网络公共事件的定义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就“公共性”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据,指出这一词源上可溯至古希腊,以及其作为具体概念在近代的嬗变史。而公共事件在中国肇始于晚清的“杨月楼事件”,《申报》对这一事件及其后“杨乃武案”的长时间报道开启了中国公共事件的发展史,这与新闻业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后,在对“假事件”“媒介事件”与“新媒体事件”等概念进行观照后,作者通过大量查阅文献并结合网络发展实际情况,明确了网络公共事件这一概念的几个特征——事件公共而非公开、与特定突发事件相关联、过程动态但时间持续,可以被划分为维权性、曝光性、抗争性等类型。
而揆诸本书的研究视角,元语言理论的溯源亦显得不可或缺。作为“meta”这一颇具黏着力的概念与“语言”组成的词汇,元语言的研究与20世纪初期的“语言学转向”密不可分。作者分类、引述并梳理了罗素的分支类型论与语言分层思想、塔尔斯基的对象语言/元语言区分与语言层次论、卡尔纳普的逻辑语义学与语形语言论、波普尔的语言四功能论及霍尔、艾柯、雅柯布森与国内赵毅衡教授等关于元语言的研究理论,形成了清晰的元语言研究图谱,为其后的分析内容奠定了学理基础。
二、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权、元语言问题与符号学分析路径
皮尔斯将“再现体”(representation)、“解释项”(interpret-ant)与“对象”(object)视为符号的三元组合,体现了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的思想,而网络公共事件的分析中,这一思想与福柯与罗兰·巴尔特等人的思想都为本书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的作用。围绕本章的“话语权”问题,作者首先引述了斯蒂文·李特约翰认为“话语是传播的产物,具有社会属性,是由符号构成的”这一观点,进而讨论了本章中最重要的、福柯的话语权力观。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实践—符号”的概念而非语言符号本身。因此,网络中的话语主体在传播交流中也会意图利用话语确立地位,从而自然引出了所谓“话语权”的问题。这一理论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陈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并以此确立社会地位。所以实际上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通过话语权力才得以实现。在其后的论述中,作者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在作者看来,福柯和其解构主义思想对于话语的差异性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是其对权力的分析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往往还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话语的本质,而实际上话语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并非完全是权力的产物。因此,实际上掌握了话语权就是掌握了社会行为的规则,是一种元语言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的体现。在其后网络社会阶层的划分上,本书作者将其划分为三类,掌控网络媒介的精英阶层、网络媒介的使用阶层以及网络媒介的边缘阶层。
在明确了网络公共事件主体(“自我”与“身份”)与客体(话语权表达涉及的对象)后,作者开始谈及元语言控制下的话语权表达。本节首先介绍了组合与聚合、双轴关系与符号表意过程几个因素作为主导的一些相关符号学概念,从而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网络公共事件符号文本在生成与完成的全过程中的聚合与组合情况。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新视角——将元语言和话语权二者放在一起来比较研究,认为元语言始终为话语权“背书”,网络公共事件争论的背后原因也都是元语言,亦即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进行元语言的争夺。由于网络话语的权力效应,实际上传播的权利归属已经由传统媒体转向社会公众。在“媒介化”的社会背景下,似乎社会各方都在争取优先受众群体,抢夺“传统媒体的话筒”,作者指出这看似是一场“庶民的胜利”,却都把焦点集中于“话语权”而忽视了其最终的指向——元语言。
通过以上的论述,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与元语言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足够清晰明确,紧随其后的就应是对其分析的符号学路径进行讨论。作者认为网络公共事件的传播有两种不同路径——分别是“以传统媒体为主”与“以社交媒体为主”。以传统媒体为主的路径中,作者主要介绍了“广西南丹7·17事故”“孙志刚事件”“马加爵事件”等,认为这些事件都是个人议题经由网络论坛和传统媒体的同时段报道,从而扩大成为网络公众的自我议题设置,最终成为社会舆论;而以社交媒体为主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作者选取了“唐慧事件”“魏则西事件”等事件,提及了2016年后传统媒体传播路径的式微与以社交媒体传播为主的网络公共事件的一般路径,认为这些公共话题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感性认知与纯粹宣泄过渡为理性思考。
在讨论这类事件时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略,也就是这类事件的命名。作者认为命名是一个符号学问题,是人类通过符号化行为来完成的,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实际上表征着本书的一个重点——符号的理据性问题。作者紧扣本书重点,借邵敬敏提出的“框式结构”,提出这一结构的呈现究其原因仍是基于社会文化的元语言因素。而有符号的提出自然有符号的识别与解读,在识别方式上,作者引“标签理论”,指出了让单个符号在文本使用过程中获得理据性的手段,亦即这类事件命名的重点——“贴标签”。作者辩证地解读了这一行为,认为其简化了人们的认知过程,但带来了“预设立场”等弊端。而在本书第四章中作者提及的符号宰制权,即给某一具体事件冠以某种“关键词”的行为亦与之有相似之处,只是这种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其实更偏向于下文中提及的“元语言争夺”的一个显性表征。最后,作者介绍了网络公共事件再现的两种主要方式:文本重复,即以数量上的简单累积来达到使符号重复由量变发生质变,增加理据性的过程;另外一种是网络模因与媒介再现,这一部分作者首先引述了弗朗西斯·海拉恩的模因传递四阶段,提出了网络公共事件从个案转化为焦点的三个特征:道德伦理、情绪带入与情感-理性的转变。在媒介再现上,作者第一次引述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指出每一个事件的媒介再现已经先入为主地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看到的网络公共事件实际上已是一种被再现的结果。
三、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争夺、离散与真相
元语言的存在使文本之间能够互相翻译,互相理解,也强制了任何一个文本得到至少一个解释意义。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各方观点表达与话语权的斡旋背后实际上是元语言的争夺,因此作者就元语言在信息传播时的意义建构这一过程中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探究。
意指系统在第一系统进入第二系统后形成的内容或所指就是元语言,而当一个系统成为另一个系统的意指表达面时,含蓄意指的复合系统便由此出现。在这一系统中,隐喻是其得以实现的手段,也同样是新闻建构的重要手段。而在元语言的建构中,意识形态则起到了“看不见的手”的一种“笼罩”的作用,它是一种“文化的元语言”,既具有“整体性”也呈现出相对散乱的状态,需要通过大众媒介进行提升与延展。而文化本身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概念,援引A·L·克洛伯、K·克拉克洪、S·普芬道夫及中国古代典籍中《周易》《礼记》《说文解字》与《论语》中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作者厘清了本书核心中“元语言”中易混淆的一些概念,认为正是由于元语言的驱动,才使得文化自觉得以成为可能。
作者采用了符号互动论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互动行为进行研究,认为这一互动是基于媒介文本展开的,存在三种不同的、明显的互动形式。首先是仪式性抗争性互动,这一概念首先由詹姆斯·W·凯瑞引入传播学视阈,指出传播即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对距离与人的控制是在空间发布和传播的过程中完成的,本观点强调一种文化的共享;而仪式性抗争互动的提出同样也基于这一观点,即以某种既定的仪式行为和仪式符号来表达某种社会负面情感,揆诸本书的情境,则是以网络为媒介、通过具体事件来表达个体对社会的愤怒与不满,如2013年的“城管事件”;情感互动上,乔纳森·H·特纳认为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的驱动。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以理解,但互联网的存在让这一互动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其“特殊的情境”得到发挥,让反讽成为更多的、更有效的表达方式。作者认为,情感互动可以分为“戏谑”与“共情”等模式,网络公共事件的参与者用诙谐、戏谑的非主流表达框架对主流话语形式进行对抗,从而增加了舆论的“幽默”色彩;而由于当下网络公共事件表现出的强烈的新媒体语境特征,诸如简·梵·迪克等学者已将媒介网络视为社会环境本身,作者引尼尔·波兹曼、马克·波斯特等人的论述,认为“修辞”的互动,包括狂欢、奇观化叙事与媒介恐慌都会使传播的风险性大幅度增加。
不难理解的一点是,伴随着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总是在变化,因此网民作为信息的发出者、渠道与接收者有时会促成一种奇迹般的“蝴蝶效应”。作者认为,自媒体时代让传统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垄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观点僭越、舆论失焦的风险,这些都是自媒体时代中特殊的媒介文本。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文本?作者认为采取赵毅衡教授提出的“伴随文本”“解释漩涡”与“元语言集合的离散”等概念进行解析颇为适切,因此本章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网络和受众三个层面详细阐释了这些概念的具体表征。
尽管以上的讨论均紧密围绕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展开,但我们更关心的往往是“真相如何体现”与“现实如何被改变”。因为事实可能有很多,但真相却只能有一个。因此,作者回溯了本书第三章的拟态环境思想,首先就媒介建构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讨论与思考。皮尔斯认为人利用传播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取真相,但这是一种社群的真相,并不掌握在个人手中,这也是人的符号传播行为是社群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元语言在媒介建构现实的过程中起到相对重要的能动作用。对大数据时代的算法,作者则持辩证否定的态度,认为算法使元语言被窄化,是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比喻的印证。最后,作者对后真相的概念表示了关切,认为“后真相”时代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紊乱,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才能使得网络公共事件的冲击得以控制与缓和,从而观照了本书的撰写根源。
四、结语
媒介映射社会,媒介引领社会。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让“万众万物皆媒”的时代成为现实,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的“前台”与“后台”亦日益模糊。本书开创性地将元语言纳入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将焦点投射至其话语权建构的背后力量,并从符号学角度阐释了诸多的因素。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元语言问题颇具中国特色,研究并解决这种问题对推动当前网络与现实秩序的良性发展大有裨益。总的来说,全书视角颇具创新性,六个章节内容前后紧密关联,环环相扣,逻辑思路极为清晰。完成本书的阅读后,读者或许能对互联网上司空见惯的公共事件产生一些全新的视角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