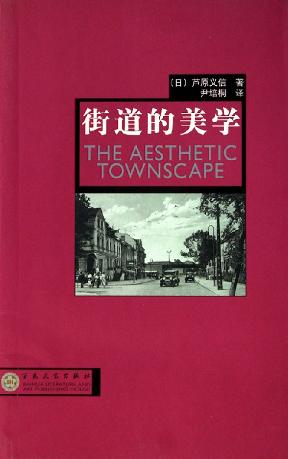
人们一向通过感知内嵌在空间内的时间流来把握自身的存在,而进入经验主体视域感知范围的,莫过于一个立体化的生存空间。赋予文化场域特定意义方式,从而在混沌的元世界中定位终极价值本源的方向性矢量,正是经验主体在前人不断积累的文化经验及传统不断嬗变,快节奏的都市资本意义空间流转之下,摸索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及对“真实”的界定的新型生存样态。
翻转的元风景
——简评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之空间叙述
人们一向通过感知内嵌在空间内的时间流来把握自身的存在,而进入经验主体视域感知范围的,莫过于一个立体化的生存空间。赋予文化场域特定意义方式,从而在混沌的元世界中定位终极价值本源的方向性矢量,正是经验主体在前人不断积累的文化经验及传统不断嬗变,快节奏的都市资本意义空间流转之下,摸索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及对“真实”的界定的新型生存样态。
都市空间是现代资本可视化的外部空间表征,然而这种文化空间却正在悄然改变物理空间。亦即特定文化形态渗透甚至是创造了新的交互性文化场域。建筑物带有强烈风格印记,是主导建造者认知模式内在符码规约的空间把握方式发挥作用下的文化产物。建筑物最初是具备“物”的使用价值的人工制成品,然而其本身就切割了物理空间,携带着特定文化形式的意味。其作为文化符号的可视载体,直接跳过对象,指向解释项终端。虽然建筑的体系延伸出街道、城市,乃至于划分地理空间的层层能指分节,然而这一人造意义空间仍就忠实记录下了经验主体的感知模式。
日本建筑学家芦原义信的著作《街道的美学》,从制约东西方文明的文化符码入手,直取空间构成的心理机制之源,即文化的 “原风景”,试图探寻隐藏在建筑物视觉表象之下的文化元语言。笔者认为此处的“原风景”,即意味着一个元语言层面上的空间符码集合,制约着建筑风景的构成方式及其形态特征,故称之为“元风景”更为贴切。
芦原义信深入剖析了意义空间在视觉能指形式上所具有的美学价值,这不失为独树一帜的元层面分析。作者列举构成建筑空间基本概念的墙、门、柱等意义空间,从街道、广场、花园、功能分区(如住宅区、商业区),到室外雕塑、夜景空间、地标建筑,广泛涉猎日本本土及西欧各国的经典或是现代建筑,并实地测量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对比,总结出一系列颇值玩味的建筑空间理论。以下笔者取其一、二分别探讨。
1、墙:区隔空间场域的结界。构成建筑内部空间的基本条件是边界概念的实体化,边界所承担的首要意义,便是 “内部”与“外部”的认知。墙,这一支撑性的力学结构,自然构成了不同意义空间的一道有形区隔。有形的墙壁承担着人造建筑物,与外部物理空间的区隔功能。墙内是意义秩序的内部,反之,墙外则是意义秩序的外部。
以西欧砖石结构建筑为例,厚实的墙壁在空间及心理上都是一道区隔内外意义秩序的结界,一种防御性的精神结构,区隔了家庭私用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而日本土木结构建筑则打破这一原则,墙极薄且不确定,可以说是一道非实体化的心理“结界”。介于梁柱之间的一块块开敞空间,皆可成为临时的流动性“墙壁”,内外的空间则主要靠玄关的脱鞋处来区隔。日本式建筑从本质上即否定实体性“墙”的存在,相较于西欧高视线站立的“墙型文化”,更为偏重于低视线坐式的“榻榻米文化”。
2、消失的轮廓线。街道两侧由连续建筑物的外墙所构成的轮廓称为“一次轮廓线”,由建筑物本体延伸出来的链文本,(即建筑的附加部分,如商业街的广告招牌)构成的轮廓则称为“二次轮廓线”。[①]街道的一次轮廓线愈清晰,则其视觉形式愈整齐美观;与之相反,若是二次轮廓线首当其冲,经验主体则难以把握住一个统一的意义形态空间。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现代工商业大城市,二次轮廓线往往占据了绝大部分视野,这意味着商业广告促成的符号消费正在不断蚕食着人们对生存空间的既定认知,意义场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经验主体则迷失在灯红酒绿的霓虹招牌之间。一次轮廓线不断由二次轮廓线所取代,建筑的形式意味逐渐趋于一致,大量“火柴盒”如同生产线上的工业制成品一样,机械平庸。反观古典建筑,大多具有富丽堂皇的“正面性”,及左右对称的“纪念性”,其在设计建造之初便已考虑到超出物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审美价值及历史文化价值。
3、翻转的空间。格式塔心理学认为,进入视线认知范围的 “图形”需要一个背景来称托,方可形成视像经验,而作为参照的“背景”亦可翻转为“图形”来视认。也就是说,“图形”和“背景”互为阴阳,虽同时存在但不可同时被认知。芦原义信借用道家“阴阳学说”与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了“阴角空间”,和“阳角空间”的概念术语。[②]
所谓阴角空间是向内收敛的封闭性边界,而阳角空间则是向外突出的扩散性边界。向外凸出的阳角空间随处可见,如建筑物的外墙转角,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排斥性,易于引起区隔注意的意义空间。而阴角空间则完美的隐藏了边界,形成一个向心收敛的外部封闭空间,是一种提供了包容性与聚合度的意义空间。以意大利广场为例,在欧洲广场政治传统的背景下,广场成为交互性主体进行碰撞、融合的场域,并提供多种公共性功能的使用。广场构成的内嵌式阴角空间完全可以作为“图形”,与建筑自体所提供的“背景”进行翻转。作者将这种可翻转的空间称为“积极空间”。然而以传统东方村落建筑为代表的阳角空间,则不具备和作为“背景”的自然环境物理空间进行翻转的功能,若将散点状的村舍作为“图形”视认,一旦外部自然环境与之翻转,便几乎消失于自然野趣茫茫“背景”之内。作者又将这种不可翻转的空间称之为“消极空间”。[③]
可翻转的城市空间是轮廓清晰的,作者认为大多数西欧城市都具备这种可翻转性,然而以江户城为代表的日本城市却是阙如。若将其“图形”与“背景”翻转,则会发现象征将军权力的政治文化中心——天守阁,是一个虚空的中心。正如罗兰·巴尔特在其名著《符号帝国》[④]中所言,日本的城市就如同其文化性格一般,缺乏中心性,就像没有骨骼的软体动物一样可以无限次的拆毁重建,佛教深厚的“无常”观念及虚无传统,导向了一个意义空间场域的“空无”。
综上所述,经验主体在不断创造文化空间的同时,也加深了意义解读的编码强度。建筑物借助外部物理空间的视觉再现,隐藏了经验主体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文化符码规约。要想理解其存在形态的意指方式,恐怕不可忽略制约其运作机制的元语言。通过 “翻转”空间获取别样的意义解读,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被重新清理,开启了意义的另一种可能性。而这或许正是冲破空间结界,叩开通向解释项终端的另一扇“门”。
作者介绍:李露茜,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