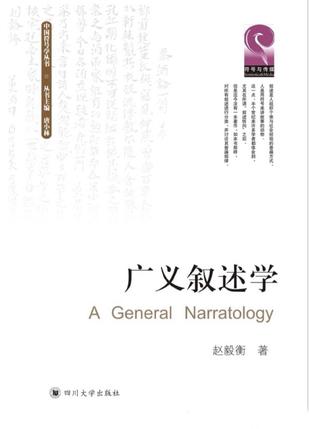
叙述学从196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阶段,目前面临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广义叙述学阶段。当前的叙述学研究已经远远突破文学领域,向法律、教育、历史、影视、传媒网络、广告等等领域扩展,已经形成规模宏大的“叙述转向”,叙述学研究,无论经典还是后经典,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叙述转向的发展实际。
叙述学从196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阶段,目前面临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广义叙述学阶段。当前的叙述学研究已经远远突破文学领域,向法律、教育、历史、影视、传媒网络、广告等等领域扩展,已经形成规模宏大的“叙述转向”,叙述学研究,无论经典还是后经典,都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叙述转向的发展实际,因此,建构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框架就成为叙述学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无疑是一重要收获,“经过叙述转向,叙述学就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既然许多先前不认为是叙述的体裁,现在被认为是叙述体裁,而且是重要叙述体裁,那么叙述学就应当自我改造:不仅要有处理各种体裁的门类叙述学,也必须有总其成的广义叙述学。”[①]为了能够清晰理解赵毅衡建构广义叙述学,因此,建构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框架就成为叙述学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无疑是一重要收获,“经过叙述转向,叙述学就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既然许多先前不认为是叙述的体裁,现在被认为是叙述体裁,而且是重要叙述体裁,那么叙述学就应当自我改造:不仅要有处理各种体裁的门类叙述学,也必须有总其成的广义叙述学。”[①]为了能够清晰理解赵毅衡建构广义叙述学理论框架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叙述学发展阶段的递进历程,然后从学科历史层面建构叙述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框架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叙述学发展阶段的递进历程,然后从学科历史层面建构叙述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 叙述学研究范式及其变革
叙述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并非是一个偶然,而是历经了长期了历史铺垫。叙述,作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伴随人类始终,从远古的岩画到今天的网络游戏,叙述无处不在。叙述是人类建构自身生存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将时间经验、空间经验进行逻辑化、因果化的过程。因此,从岩画记事、结绳记事、绘画记事、文字记事、录音录像记事到现在的数码记事,记事方式的更新变化无不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人类也在探索有效的记事方式和记事方法,因此探索记事本体的叙述理论也源远流长。西方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以及后来的移情说、游戏说等等无不想从各种方面揭示人类文学艺术的产生原因。而对于叙述的研究则在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之后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中国,诗歌是文学的正宗,小说被斥为道听途说的“小道”予以贬斥,不登大雅之堂。因此,以小说叙述为核心的叙述理论则到明代以后才得以发展。在西方,真正引起理论家对叙述理论关注的则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开始。然后出现所谓小说美学的“首次崛起”的三部小说理论著作:珀西·卢伯克《小说技巧》、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和埃温德·缪尔《小说结构》。在中国则有金圣叹、毛宗岗、李卓吾、紫砚斋、冯梦龙、凌?鞒醯热说男∷道砺邸K?姓庑┒嘉?鹗鲅У牡??隽顺浞值睦砺圩急浮?span lang="EN-US">
进入20世纪,在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等的影响下,叙述研究进入了第一次范式革命,即由原来的外部研究转向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探索共时状态下所有文学叙述作品的内在结构和话语规律。1969年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述学”概念,标志着叙述学的正式诞生,这是叙述研究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之后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叙述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布雷蒙、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等等,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为经典叙述学研究划出了理论边界、建构了一整套的理论规范、范畴,形成一套较为严密的叙述学理论体系。清晰的理论表述和可操作性为叙述学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并迅速成为一个地位显赫的理论通行世界。
中国叙述学研究较为充分地吸纳了经典叙述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一批叙述学家,如赵毅衡、申丹、胡亚敏、谭君强、罗钢、杨义等等。随后,经典叙述学在20世纪后期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冲击下开始走向反思与突破。199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叙述学研究的小规模复兴,政治与意识形态批评融入了叙述学研究,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的理论侵入为叙述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空间。叙述学研究进入第二次范式革命,叙述学研究开始从经典叙述学的封闭走向后经典叙述学的开放。但,叙述学这种借重其他理论的研究范式必定为其他理论的发展所局限,叙述学研究似乎在“复兴”之后又进入了另一个范式瓶颈。与此同时,叙述研究已经悄然发生着另一种变革,即来自非文学领域的“叙述转向”,为此,叙述学界显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首先发生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叙述转向”波及教育、医疗、法律、影视、广告等等各种领域,其规模之广、领域之大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叙述学研究。换句话说,叙述学研究进入其发展的第三阶段,面临第三次范式变革。
在“叙述转向”的现实语境下,叙述学研究必须冲破以文学文本为对象的狭隘圈子,走向更广阔的领域。罗兰·巴尔特在《叙述结构分析导言》的开始提出的叙述无处不在,各种领域都存在叙述{C}[②]{C},但,无论经典还是后经典叙述学研究,实际上并非关于叙述的一般性理论,而是“文学叙述学”。也就是说,叙述学研究并没有为“叙述转向”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叙述学研究已经进入第三次范式变革。美国理论家伯格在《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中指出,“世界上叙事数量几乎数不胜数,但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对它们进行分类,这样潜在的读者(电视观众,电影观众,戏剧观众等等)就能知道应该期待什么。”{C}[③]{C}伯格按照“样式”对文本进行分类,并由此规划出了一个“抽象的阶梯”:
叙事理论
(关于所有种类的叙事的本质的理论)
↑
叙事样式
(例如电视节目:科幻电影、西部片、
情景喜剧、侦探片、肥皂剧、新闻节目、广告)
↑
叙事文本
(所有的存在叙事文本){C}[④]{C}
伯格的“抽象的阶梯”勾勒了叙述理论发展的一般图示,但当“叙事文本”跨越“叙事样式”最后形成“叙事理论”时,存在两种发展方向:其一是关于所有叙述文本的叙述理论;其二是关于某一叙述类型的门类叙述理论。广义叙述学要做的是前者,即就叙述的一般性做出理论概括,也就是说,在“叙述转向”背景下找到叙述文本共同的理论基础。当然,伯格关于“叙事样式”所列的各种叙述类型并非“全域性”分类,挂一漏万,而且他的分类也没有给出学理性的依据。但我们无法对伯格的研究做出超越性要求,因为,他是在“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中展开研究的。但伯格的“抽象的阶梯”至少提示我们,建构一般意义上的叙述理论已经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给出了耳目一新的答案,即在“叙事文本(所有的存在叙事文本)”基础上建构一般意义上的叙述理论研究框架:广义叙述学。因此,叙述学研究必须面临再一次的范式变革,我们必须抛弃叙述学研究的既有成见,重新审视叙述的基本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全域性的叙述分类,并建构一般意义上的叙述学研究框架。因此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无疑开启了叙述学研究第三次范式变革的序幕。
二 广义叙述的理论框架
在“叙述转向”背景下,打破叙述学研究僵局,改变经典叙述学文本封闭式研究和后经典叙述学理论浸入局面,必须对叙述进行进行一般性的分类和概念界定,这是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学理基础。赵毅衡认为,叙述学是符号学的分支,从符号学视角考查叙述学,可以为广义叙述学的学科建构提供思路。首先,赵毅衡在本书“前言”部分对所有叙述进行了分类与说明。按照本书观点,叙述分类按照纵横两条轴线展开,“一条轴线再现本体地位类型,即纪实型诸体裁/虚构型诸体裁;另一个轴线是媒介-时间方式”,“如此一纵一横,所有的叙述体裁都落在这两条轴线的交接处:每一种叙述,都属于某种再现类型,也属于某种时向-媒介类型”。(赵毅衡,3)这样,每种叙述类型都找到了各自的坐标。实际上,这种基本的叙述分类原则为《广义叙述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
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另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打破传统叙述学研究的“体裁自限”、解决来自叙述学自身发展和“叙述转向”双重压力(赵毅衡,5-6),为“叙述”扩容,即重新定义“叙述”。赵毅衡给出了叙述的“底线定义”:
一个叙述文本包含由特定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
{C}1.{C}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
{C}2.{C}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赵毅衡,7)
以上述叙述分类与最简叙述定义为基础,《广义叙述学》以“总-分”的结构逻辑建构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大厦。在“各类叙述”中对“叙述分类总表”中的叙述类型的分类原则进行了论述,指出“文本意向性”是最基本的分类原则,“文本是体现主体间关系的符号组合,在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有一定的意向关系,这种意向体现为意义和时间的方向”,“所有的叙述文本,都靠意向性才能执行最基本的意义表达和接收功能”。(赵毅衡23)。按照意向性和“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可以把叙述体裁分为三个大类:记录、演示和意动,然后在三种时向和纪实与虚构的纵横坐标交叉形成具体的各类体裁。以此分类原则为基础,本书就“演示类叙述”、“心像叙述”和“意动类叙述”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从而为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叙述分类原则和学理框架提供了可操作的基本原则。
对“真实性”问题的探讨一直是文学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一般的理解往往把艺术合理性作为“艺术真实”判断的标准,并时常将之与客观现实进行对应。但在叙述转向背景下,这种理解往往带来困惑,因为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在接受层面构成的交叉使我们难以找到自己的坐标。《广义叙述学》对纪实型与虚构型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双区隔”原则,框架区隔为“现实性”提供了另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即使是虚构文本,“在同一区隔中,再现并不表现为再现,虚构也并不表现为虚构,而是显现为事实,这是区隔的基本目的”。(赵毅衡,81)。也就是说,关于文本区隔范围内的事实性并不具有外指性,它不对应区隔范围之外的客观事实。因此,在任何框架区隔之中,“虚构只是对虚构外的世界是虚构”(赵毅衡,83),而对于虚构框架内的世界则具有足够的真实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会沉浸其中,并相信那个虚构的世界。当然,没有人会在《红楼梦》的虚构世界之外去寻找贾宝玉、林黛玉,因为,跳出文本体裁所设定框架区隔,故事中的人物则不会与现实形成对应。这种区隔原则维持了叙述虚构作品的合理存在,并丰富了我们的心灵世界。
对叙述者的讨论一直是叙述学研究的基础,一系列叙述学概念无不围绕叙述者展开,如叙述人称(第一、二、三人称叙述、全知叙述等等)、聚焦、(不)可靠性、叙述交流等等。但叙述转向之后,叙述迅速扩容,对叙述者的认识重新成为焦点,因为,在某些类型的叙述体裁中,叙述者究竟是什么,甚至有没有叙述者都成了问题。《广义叙述学》第二部分 “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 分三章成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叙述者,按照以往叙述学研究的“惯例”,似乎并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叙述者是一个真实存在或能够感觉到存在的叙述人格,但当叙述成为很多体裁的话语存在方式的时候,叙述者并不是一个可以直观所见或者易于判断的人格。比如,电影的叙述者是什么?体育叙述的叙述者是什么?游戏叙述的叙述者又是什么?建构广义叙述学,在叙述扩容和分类框架的基础上,找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的第一步就是寻找叙述者。作者提出叙述者的“人格-框架”二象,就是说,叙述者在某些叙述类型中表现为一个(或多个)人格,而在另一些叙述类型中则表现为一个叙述框架,比如上述几种类型的叙述者就表现为一个叙述框架。“框架叙述”可以有效解释演示类叙述,如戏剧,作为开场的铃声构成叙述开始的标志,意味着下面的叙述只对这个框架有效,一旦框架内或外的因素介入叙述就会对框架叙述构成破坏,如舞台下的观众闯入舞台之上、演员跳出角色与观众交流等等。再如体育叙述,如果赛场外因素突然介入比赛,所形成的后果要么中断比赛、要么清除介入者,介入者的出现等于破坏了叙述框架。
对于源头叙述者,书中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考查方法:文本构筑、接受构筑和体裁构筑。“叙述者就是由此三个环节构筑起来的一个表意功能,作为任何叙述的出发点”。(赵毅衡,93)。值得注意的是,《广义叙述学》提出了“二次叙述化”概念,指出,一次叙述“发生于文本构成过程中”,二次叙述发生于文本接受过程中。作者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二次叙述,并对其作用进行论述。二次叙述的提出适应了叙述转向和叙述扩容需要,同时也使广义叙述学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视域,它释放了接受者在叙述中的作用,作为可以有效解决某些叙述的构成方式,比如游戏叙述等。“故事”与“话语”是叙述学的基本概念,叙述学界对此的提法很多,语出多门,混乱不堪。更为要紧的是,此一对概念的背景是经典叙述学,文本框范使其无法释放更大的理论能量。《广义叙述学》提出 “底本与述本”,厘清学界混乱的表述方式而统一于“底本与述本”的清晰表述,并从双轴关系的角度建构了底本与述本的关系,提出的“三层次论”:底本1:材料集合;底本2:再现方式集合;述本。(赵毅衡,141)这等于把经典叙述学以“故事”和“话语”划分叙述层次的文本封闭性打破了,底本概念的引入使文本层次具有了历史内涵,这对于民间故事、历史累积型文本,以及叙述经验的累积与传承等在述本中的表现方式等均具有意义。
时间与情节是叙述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在广义叙述学研究中,却成为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叙述学研究的传统一般把叙述的时间问题置于“过去时”范畴,但广义叙述学研究中,就不得不打破这种“过去时”篱笆而向现在和未来开放。这在《广义叙述学》开篇对叙述的最简定义和叙述分类中有明显体现。第三部分就是解决广义叙述学背景下的时间和情节问题。本部分分别论述了时间在各种叙述类型中的表现形态,情节问题,实在世界、虚构世界和可能世界的“三界通达”性,以及情节的动力问题。
《广义叙述学》第四部分论述叙述文本的主体冲突。本部分对叙述学的一些常见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隐含作者”概念是叙述学跨越经典和后经典阶段的基本概念,争论较多。布斯作为“隐含作者”概念的提出者并不能左右该概念歧义歧出的局面,布斯后来不得不发表《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来捍卫其“正统”观点。{C}[⑤]{C}但这并非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一个概念的认识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概念的发明者,而是取决于概念所包含的学术可能性。史例极多,在此不赘述。《广义叙述学》针对叙述转向背景下的隐含作者问题,提出“全文本”和“普遍隐含作者”概念。在广义叙述学背景下,文本并非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而是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些“伴随文本”会参与文本整体性的建构,同时接受者的参与也会成为文本的一部分,所谓“全文本”就是“进入惯例式解释的全部文本元素之集合”(赵毅衡,220)。而本书对隐含作者的界定基本站在认知角度。对于任何表意文本而言,“必定卷入文本身份,文本身份需要一个拟主体集合,因而就必须有一个‘发出者拟主体’,即‘隐含作者’,作为文本的意义-价值集合,此时可以称作普遍隐含作者”。(赵毅衡,221)。
本书对叙述的“不可靠性”进行了探讨,不同于以往的叙述学研究传统,这种探讨是站在叙述的一般意义上的讨论,适用于所有叙述文本。对于任何叙述文本而言,判断叙述者的存在、叙述者的倾向性(思想感情、价值、意识形态等等)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里有隐藏、有伪装,刻意暴露者极少。《广义叙述学》提出叙述框架的“人格填充”概念,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该书对叙述框架中的人格填充进行了分类论述,各种形式的人格填充为叙述者的人格存在锚定了位置,并为辨识叙述人格找到了依据。“叙述分层” 是叙述学研究的另一热点,在一般叙述框架下讨论叙述分层,尤其对以往叙述学研究不太关注的演示类叙述的层次问题、时间问题进行了探讨是该书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方面。该书还讨论了元叙述,对叙述本身进行思考,让叙述本身成为被叙述的对象,这是作者集团和接受者集团成熟的表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理论对理论对象的侵入,或者反过来,理论对象对理论的戏仿,这亦然成为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而出现在多种叙述类型之中。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建构了一般叙述理论框架,从总体的理论架构,到对主要理论概念的细部描绘都给出了细致的理论图谱,为叙述转向背景下叙述的一般性研究提供了学理基础。当今世界,全球化加速,似乎很难再做一种自我封闭性的“民族性”的理论建构,也就是说,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语境压力:我们要么继续“跟着走”或者“接着做”,要么必须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这并非是说我们没有民族性优势,赵毅衡这本书就指出,从中国文化特质方面说明,中国语言无时态性更有利于广义叙述学的研究,因为,西语的时态性使西方众多叙述学家纠缠于“过去时态”而把大量的叙述体裁(如演示类、意动类)排除在叙述学研究之外。这种文化自信更来自先生对中国学界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与改变中国学界“接着说、跟着说”局面的勇气与智慧:
中国叙述学界还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全局性的新课题。原因倒也简单:西方叙述学界尚未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真的必须留在一百年来的旧习惯之中,只能让西方人先说,我们才能接着说、跟着说吗?难道中国学界至今没有提出新课题、思考新课题的能力?{C}[⑥]{C}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建立学术自信也许比学术本身更有价值。因为百年西学所形成的学术惰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合法化”、体制化的东西,渐渐渗入中国学人的潜意识之中,创新倒成了“异端”!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打破叙述学研究的自我“茧壳”,在“叙述转向”的语境下,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学科框架,无疑掀起了叙述学研究继经典与后经典之后的第三次范式革命,并预示叙述学研究第三阶段的到来。
三 广义叙述学的未来
广义叙述学的提出背景是规模宏大、既成事实的“叙述转向”,面对叙述向多种领域渗透,叙述学界显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面对如此规模的叙述转向,来自语言学、形式主义学科背景的叙述学显然无法应对,既有的叙述观念、研究框架无法为多种类型的叙述提供学理性框架,因此,应对叙述转向必须有一种全域性的视野作为支撑。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站在符号学视角进行理论建构就回避了语言学、形式主义的学科局限,为各种叙述类型提供一种共同的理论框架。
但应当指出,叙述转向只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说法,各种领域对叙述的运用并非具有相同的模式。对于很多领域来说,叙述转向只不过运用叙述的方式促进本领域的研究。比如医疗叙述,就是让病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叙述的方式呈现问题,建立病人自己的人生经验逻辑,医生从中发现问题,引导病人建立人生自信等等;再如教育叙事,就是让受教育者或者教育工作者以叙述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生活、工作的心理秩序,从而健全人格。也就是说,叙述对于这些领域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其研究的对象,他们的目的只是通过叙述这一工具抵达各自的研究目的。但对于叙述学研究者来说,这并非他们的研究范式。叙述学研究就是以“叙述”本身为对象的研究,这与把叙述作为研究工具具有本质不同。对此,赵毅衡指出,叙述转向包含了三层意思:
把人的叙述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心理学中尤其明显);2.用叙述分析来研究对象(在历史学中尤其明显);3.用叙述来呈现并解释研究的发现(在法学和政治学中尤其明显)。不同学科重点不同。(赵毅衡,13)
无论怎样,叙述学必须面对叙述转向给叙述学的学科发展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迎接这种挑战,否则,叙述学就真的会在自我封闭中走向死亡。《广义叙述学》无疑成功地应对了这种挑战,正像本书指出的那样,“叙述转向使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考察,在广义叙述学真正建立起来后,将会是小说叙述学‘比喻地使用’广义叙述学的术语”。(赵毅衡,17)这意味着,叙述学在历经经典和后经典之后,为迎接叙述转向带来的学科挑战而进行的又一次自我调整,是叙述学发展的第三次范式革命,并预示着叙述学研究第三阶段的到来:广义叙述学阶段。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无疑具有开创性。广义叙述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意味着以后的叙述学研究很难再返回以文学叙述为研究对象的经典叙述学与以理论侵入为特征的后经典叙述学轨道上去。因为,传统叙述学研究那种对叙述概念的“默认程序”已经被打破,文学叙述研究在广义叙述学的学科框架中成为一种类型研究而不具有普遍价值。
笔者认为,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在叙述转向背景下建构了一般叙述的学理框架,对于叙述学研究来说,第三次范式革命这才刚刚开始。判断一个学科的发展前景首先必须看这个学科所建构的学理基础是否足够抽象,即摈除个性找寻共性;其次看这一学科的“吞吐量”,即是否具有全域性。论述至此,笔者愿意再次回顾本文开头提到的伯格的“抽象的阶梯”,当我们跨过“叙事样式”的门类叙述研究,从全域性的叙事文本抽象出“叙事理论”的时候,意味着在共性周围散布着个性十足的叙述类型,以叙述共性关照叙述个性,建构具有类型特性的门类叙述学,其发展潜力是惊人的。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赵毅衡对于广义叙述学的理论框架建构是建立在“形式研究”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在形式之外,对一般叙述的理论建构还远没有结束。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作为广义叙述学研究范式的双翼,预示着叙述学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后充足的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①]{C}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5-6页。本文下面对本书的引用采取引文后直接标注作者和页码形式,不再另行做注。
[②]{C} [法] 罗兰·巴尔特在《叙述结构分析导言》,《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404页。
[③]{C}[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2页。
[④]{C} 同上,33页。
[⑤]{C} 韦恩·布斯《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当代叙事理论指南》詹姆斯·费伦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3-80页.
[⑥]{C}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一个建议》,《叙事》(中国版第二辑),唐伟胜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50页。
作者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467000
Email:wangweiy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