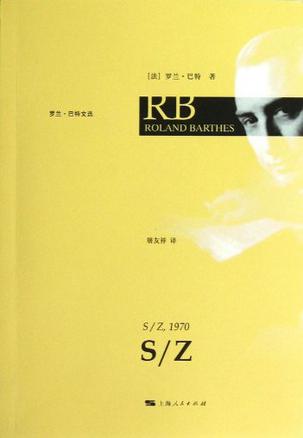
阅读,按照通常的理解,不过是一种审美式消费。然而,罗兰·巴尔特以“写下阅读”——生产性阅读、写作式阅读的新型说法,颠覆了这种观点。阅读不是寄生于写作,阅读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写作,甚至是写作的轴心。实际上,与其说巴尔特在《S/Z》中谈论的是阅读,不如说是一种新型写作。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它“是一篇文,我们抬头之际,此文写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罗兰·巴尔特:“写下阅读”
——杨利亭评罗兰·巴尔特《S/Z》
阅读,按照通常的理解,不过是一种审美式消费。然而,罗兰·巴尔特以“写下阅读”——生产性阅读、写作式阅读的新型说法,颠覆了这种观点。阅读不是寄生于写作,阅读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写作,甚至是写作的轴心。实际上,与其说巴尔特在《S/Z》中谈论的是阅读,不如说是一种新型写作。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它“是一篇文,我们抬头之际,此文写在我们自己的头上”[1]。
一、 阅读——游戏的真理
在《S/Z》一书中,巴尔特反复强调了“阅读”的性质及其目的。“我恢复的不是某个读者(你或我),而是阅读”[2]、“不存在阅读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真理,而只有游戏的真理……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积极活动起来,处于文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3]。
巴尔特的这种阅读中的游戏之真理,类似于布朗肖在其《文学空间》和《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中,对书写的无限衍义或书写的永恒的界定,“以书写等待书写”,没有阐释的主客观真理,只有书写的真理,书写既是文(文学)得以存在和运作的中心,也是它自身的内与外,书写除了自身之外,并不指向其他。德勒兹更有惊人语:“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4]。与德勒兹的说法截然相反,卡夫卡说,“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而写下来的文字,只不过是经历的渣滓。”可见,与德勒兹他们相比,卡夫卡过于强调了书写性文字的载道功能,他喟叹文字不能详尽自己的真实经历,就更说明了这一点。
布朗肖与德勒兹的观点很类似,都强调书写的持续生成性,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后者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生成理论”。说巴尔特的阅读的游戏之真理性类似于后两者,在于三者都聚焦于文学本身的可持续性书写、生产性特点——无论是释读还是书写,都是主动性生产而非被前定的消费。
正如海德格尔廓清了西方长久以来对存在与存在者的混淆,巴尔特也诊断出了阅读与与阅读者的区别性症状。相比于阅读,阅读者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说,阅读的规则是存在于阅读者诞生之先的象征结构或形式,阅读出自于“古老的叙述逻辑”,出自于“广阔的文化空间”,作为个体(不论作者还是读者),身处阅读之中,“只不过是一通道而已”。
二、 阅读——一种语言的劳作
布朗肖说,写作即命名;巴尔特说,阅读即命名。在笔者看来,此处布朗肖的“写作”与巴尔特的“阅读”很类似,都是以一套文字符码的运作机制来寻求意义、发现并阐释意义。尽管意义的阐释极有可能受阻于文字符码的含混性,容易呈现隐约的可见性,但是这并不会削减其有待破解的强大吸引力。归根结底,命名无疑是一次编码,是从迷蒙、混沌中抓取一个可能性的确定——暂时妥协于一个意义定点,以便吸引解码者前来一瞥。
阅读并不独来独往,它勾连起不同体系,在其中涡旋,穿针引线、结合、启动,却不会最后买账。阅读即发现意义(或促使意义呈现,恰似靡菲斯特在浮士德的命运中扮演的角色,发掘恶却不断地在不经意间促成善),“发现意义即命名意义;然而此已命名之意义绵延至彼命名;诸命名互相呼唤,重新聚合,且其群集要求进一步命名:我命名,我消除命名,我再命名:如此,文便向前延伸:它是一种处于生成过程之中的命名,是孜孜不倦的逼近,换喻的劳作”[5]。
巴尔特以巴尔扎克的《萨拉辛》这一小说文本作为《S/Z》全书的分析对象,并不是偶然随意为之,而是在数次阅读的感悟之上创作而成。用卡尔维诺评价司汤达笔下的主人翁的话来说,《萨拉辛》这部小说中也同样塑造了一个“一旦投入激情,浑身都是自我意识”的人物——萨拉辛。伴随这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产生的自我意识,人物的命运也有了两种可能性结局:成就——毁灭。对于司汤达来说,激情成就了人物:超脱世俗物欲,实现终极的精神追求。然而,对于巴尔扎克,激情带来的是彻底的毁灭,臆想的欲望或美之乌托邦只是死亡的美丽面纱。萨拉辛的命运结局:既是陷入爱情和艺术的自我意识不能自拔的悲剧,更是死在句法结构中的必然——换句话说,如果叙述进程无休止延宕下去,萨拉辛的死亡期限就会不断推迟,那么死神对此也无能为力。
那么,萨拉辛最终的死亡是对真相的揭示还是掩藏呢?巴尔特认为,终极的文之外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只有语法结构是否逻辑连贯才至关重要。比如说,谎言本身包含什么内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谎言是如何构成的。再如,故事讲了什么情节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情节的语义成分有哪些。因此,“不管何种情景,真相就是最终被发现了的谓语,主语最终得到了它的补语;因为人物,总显得不完整,未充满,是个四处徘徊的主语,搜寻其最终的谓语:在此徘徊期间,除了圈套、误解而外,别无显现:谜,就是此谓语缺乏的状态;揭露,话语便完成了合乎逻辑的程式,而正是这次重新找到的完整,产生了戏剧的结局:主语最终必得到某一定语,整个西方的母细胞(主语和谓语)必被充满”[6]。
三、 反“皮革马利翁主义”
借助于艺术家萨拉辛的故事,巴尔特掀起了一场新的文学批评或审美批评的革命。 巴尔特反复提及的一点是:“我们所寻求者,乃是勾勒某种写作(此处为古典写作,能引人阅读的写作)的立体空间”[7]。对于巴尔特来说,即使列出多种批评(心理学,精神分析、主题学、历史学、结构主义、传记批评、语义学、修辞学等),也不是为了强化某种批评,而是使得每种批评都可以作为倾听文的耳朵而在场。
巴尔特提出五种符码以阐释《萨拉辛》:布局符码(经验的声音)、意素符码(个人的声音)、阐释符码(真相的声音)、象征符码(象征的声音)。需要说明的是,这五种符码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聚合为一体,共同构成写作,使之成为一个立体空间。“每个符码都是一种力量,可控制文(其中文是网络),都是一种声音,织入文之内”。[8]对于歌手赞比内拉来说,他/她本身就是不断散播各类符号(美的象征、女人中的女人、永不不枯竭的艺术灵感的激发者)的源头,无论其沉默还是言说,都无法阻挡萨拉辛在他/她身上倾注全部的艺术创作激情和炽烈如火的爱情欲望。
萨拉辛是无意识中的皮格马利翁,然而他的艺术追求和爱情理想却寄托给了一个无内核的阉割者,而皮格马利翁神话所揭示的是:一位真正的女子从雕像中走出,或者更确切地说,雕像受到艺术家的至诚期许而有了生命和情感。萨拉辛也有如此期许,只不过他的激情过于盲目,倾注在了错误的对象上面,这错误驱使他于无意识间步步走向了死亡的深渊:“爱情——艺术”之幻梦同时毁灭——赞比内拉不具备任何一种给予萨拉辛欲求的可能。也许唯有在临死之前,萨拉辛才悟到,只有从虚妄中醒来,虚妄才存在。萨拉辛之于阉割者赞比内拉的不可遏制的恋慕激情,犹如歌德笔下的维特之于绿蒂,归根结底,他们爱上的不过是自己臆想中的爱情对象,是一股不可扼制的激情编织的幻梦,而不是现实中的具体某个人。投入激情的人是没有理性意识的,只有一往无前的难以名状的勇气:“我内心开辟一个战场,有决策,有行动,有战国……我从亢奋中得到滋养,我在激奋中度日,我总是个艺术家,爱把形式当成内容”。[9]
参考文献:
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2]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3]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4] 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页。
[5]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6]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2-303页。
[7]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8] 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9] 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