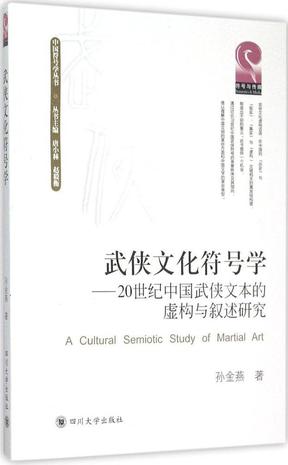
说到武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嘻哈式”的周星驰式的戏说武侠、喜剧武俠,或者是一种娱乐的动漫武俠。武俠小说,作为一种可能被寄予过载道厚望的非正统文类,一度以牵动起无数阅读者的家国情怀之文化载体而存在(当然,也不乏个人独自逍遥、驰骋纵横江湖的悠游之欲望他者的载体)。在处处渗透着现代性理念的当今时代,武侠小说似乎早已被动地退出了我们的阅读视线——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一种对英雄情结和侠骨柔情的“不成熟”的迷恋和向往。
武侠符号的前世今生
——杨利亭评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
说到武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嘻哈式”的周星驰式的戏说武侠、喜剧武俠,或者是一种娱乐的动漫武俠。武俠小说,作为一种可能被寄予过载道厚望的非正统文类,一度以牵动起无数阅读者的家国情怀之文化载体而存在(当然,也不乏个人独自逍遥、驰骋纵横江湖的悠游之欲望他者的载体)。在处处渗透着现代性理念的当今时代,武侠小说似乎早已被动地退出了我们的阅读视线——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一种对英雄情结和侠骨柔情的“不成熟”的迷恋和向往。
然而,孙金燕的《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化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也即,此刻呈现在眼前的这部学术著作——对武侠小说的前世今生之命运的集中而深刻的探讨之作,以它特有的诘问深度和思想重量,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一个武侠小说的业余爱好者,毋庸讳言,我是带着几分——对“武侠小说的内在运作机制究竟如何”的——好奇和期盼而来,它的确没有令我失望,相反,它点燃了我重新阅读武侠小说的欲望和激情。
一、 “武侠”的前世今生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的序言中,分别从时间的长久积淀、思想的持续延绵、阅读的历久弥新、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不断激发和挑战等十多个角度,对何为“经典”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说。毫无疑问,按照卡尔维诺的定义,武侠著作可以被纳入经典的范畴。
另外,陈平原等人“重写文学史”(1988)的提出与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时间(1994)相差不到十年,也说明了经典和正统文学如何定义的问题。正如韩晗等人质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应不应该收入现当代诗人写的古体诗——引起业内人士持续的学术争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更是众说纷纭、难下定论。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刘象愚于1967年撰写的《中国之侠》以及陈平原于1991年问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在某种程度上,为武侠小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一般来说,“武侠”与“江湖”几乎总是形影相随。然而,在孙金燕对此进行了词源学式的考察后发现,“武侠”最早衍义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和日本的“剑侠”扮演的角色类似。“江湖”最早出现在《逍遥游》:“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另外,笔者在庄子的《庄子▪大宗师》中,也发现有“江湖”一词,“出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之所以强调这两个词的出处,的确不排除为武侠小说寻找存在之依据的可能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其最初赋义必须要一问究竟的认知心理的激发。这就好比,我们之所以沉浸于阅读一本好书,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和审美愉悦,更在于,不知不觉间,始终存有寻找和重遇老朋友的惊讶和欣喜的期待心理。读孙金燕的《武侠文化符号学》,笔者不止一次地体会到了这种愉悦。一共有三次:《鹿鼎记》的反武侠之论;余华的反武侠、反英雄小说《鲜血梅花》的探讨;漫威系列的英雄超人形象的塑造……不得不说,孙金燕对余华《鲜血梅花》的专门探讨,虽然着墨不多,但切中肯綮,抓住了阮海阔肩负复仇重任却以漫游江湖为始终的叙述形式,展现了反武侠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之四因素的全部颠覆:行侠手段、行侠主题、行侠背景、行侠过程。虽说金庸《鹿鼎记》和余华《鲜血梅花》都属于反武侠,但是金庸似乎是对自己以往武侠著作“否定性”的推进与创新,而余华更多投入了现代人的精神漫游与无所期待也无可期待的虚无感和失落感——一种退避式的自我漫游的具体演绎。
二、“武侠”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孙金燕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精彩解读。《武侠文化符号学》涉及到的符号学理论:解释漩涡、伴随文本、文化标出、格雷马斯方阵、符号自我以及广义叙述学中的可能世界、纪实与虚构型叙述等理论。需要指明的是,本文无意于对孙金燕的所有理论阐释加以转述和评论,而是只选取其中一二进行品读。
(一)盗亦有道的“江湖”美学
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彰显的是一种人间伦理正义,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侠客的道义与暴力是同时存在的,实现道义的手段是暴力,是杀伐。江湖上自有一套秩序——现实社会秩序之外的秩序。按照正统道德价值观来说,行侠仗义是对现有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无视与僭越。然而,在武侠小说的虚构艺术之中,这种暴力和道义却实现了悖论性的并存。
能够解释这种悖论存在的“解释漩涡”说明:在同一次解释活动中,同层次元语言的组合序列,可以互相协作(如真善美或假恶丑的各自组合可以集中体现某个人的主导品格),也可能发生冲突(如美与邪恶同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洛金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丑与善良协同——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面相丑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
孙金燕借助于解释漩涡对武侠进行了解读。武侠的体裁美学是与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的秩序规则相区别的,侠士要同时遵守双重规矩:道义规矩与杀戮原则。举个例子来说,西方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杀手里昂的道义规矩就是:no children, no woman。不杀妇女儿童,这是里昂的自我行业规矩。相反,在《蜘蛛侠》第一部中,救人但不杀人,一直是蜘蛛侠的行动出发点。如果杀戮是为了拯救,那就不是蜘蛛侠的行动目的。然而,在中国武侠小说里,武侠之武与武侠之侠,即,手段和目的是同时并存的,行侠的目的是以武止戈而不是以暴易暴、复仇杀戮式的冤冤相报。《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同时面对了双重困境,身为契丹人的后代,又被大宋养大成人,辽宋交战,无论参与哪一方,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道义的抉择,他将同时担负起民族英雄和叛国逆贼的名声,最终,为了解决道义悖论,乔峰不惜杀身成仁,以死平息双方交战。
真正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境界的人,已经超脱了江湖之侠。在电视剧《少林寺》中,面对敌军来犯,所有僧人起初都是以不为之为來应对,也就是赵毅衡先生所说的,“以容忍为善则,因此任何道德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只有礼让息争是永远的善”[1]。
(二)符号错觉与虚构述真
按照艾柯的理解,符号,就是可以光明正大、一本正经地撒谎。在《围城》的结局,钱钟书也提到了时间之符号的意义指向——时钟不顾人物内心的凄楚渺茫,依然在撒着弥天大谎。原本作为时间符号的钟表,与人物的情绪本也没有太大关联,然而,一旦被置入虚构叙述的文本,它便有了意义。
将虚构当作现实,把想象视为真实,是很普遍的解读现象。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老师杨昌济问学生易永畦——将来的志向是什么,后者回答,“想当关云长大将军”。另外,面对“谁对你的影响最大?”这一问题,很多人会回答: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于连、哈利·波特、简爱、浮士德等文学艺术中的虚构人物,难道这些人不知道后者是虚构中的人物么?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也许每个人都曾经历耽于幻想、不切实际的时刻——也即“包法利主义”的时刻,托尔斯泰感觉自己是杀死安娜·卡列尼娜的间接凶手——“她要死了,不,她必须死”——安娜是俄国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牺牲品,或者一个作家在写到人物即将死亡时的辗转难眠和痛苦绝望,无一不是怀着最亲近的友人甚至自己的一部分即将永远覆灭的悲戚之感。
虚构型叙述的极大魅力在于,当读者进入文本内世界时,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已不复存在。将人物命运和情感经历自行带入到我的体验之中,我即人物,人物即我,我都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一切悲欢喜乐都衍生于——仅仅密切关注他者,并不是目的,而是意在寻找并确证他者身上的那个自我,此刻,他人已经成为了我的角色扮演,我才是真实体验那痛楚或极乐之人——所有关切之情,都由此而来。然而,詹姆逊可以旁观人物的命运,同时看到作者的虚构踪迹和人物的可见性命运,并将二者叠加,曰:人物不是死于其他,而是死于漫无止境的语句从林之中。人物死在句中,是很吊诡的事,原因在于,人物不可能意识到他与修辞的关联,人物处于修辞之中,而不是与修辞并肩而行,这只是作为解读者的詹姆逊的一厢情愿,是跨层解读。
三、 武侠符号的未来
武侠符号解读,针对的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还有它的后代,武侠影视、武侠动漫、武侠游戏、武侠文化消费产品、武侠品牌符号。
孙金燕不仅对武侠各类体裁进行了精彩的理论解读,而且也在不断地解读中发问,并且尝试着补足已有武侠批评的缺陷的同时,努力扩充武侠批评研究的视域。比如,中国的武侠符号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为什么长久地固守在本国而无法走向世界?中国的武侠符号为什么会时常被国外影视产业成功利用并反向倾销、获得甚为可观的多国票房收入?中国的武侠符号为什么不能老少皆宜,成为成年的童话?多数中国武侠符号为什么只意在传播科普知识而不是普世价值?中国的武侠符号为什么没有在幻想和创意上狠下功夫?中国的武侠符号为什么在受众接受上(受众断层)和意图定点上总是剑走偏锋?
对以上这些现象的质疑和发问力度是很大的,正视并理性反思更是迫在眉睫,是不容滞缓的当务之急。望闻问切是判断病症的前提,在此之后,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关于笔者以上多个问题的总结,孙金燕是如何探讨和回答的,读者诸君还是亲自莅临,去一看究竟吧。
参考文献: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孙金燕:《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余华:《献血梅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