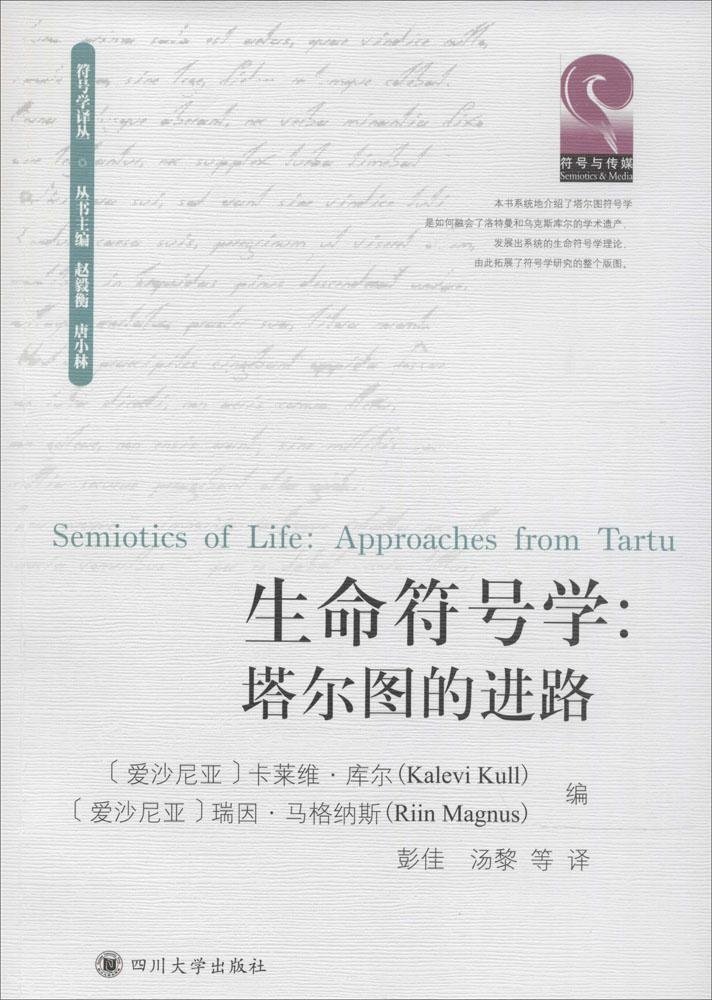
应当来说,意义在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所以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学科,其门槛也在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中得以降低。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使得符号学研究更具包容性。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学者在扩展符号学适用领域上尤为活跃。他们由起初对文化符号学的关注,进一步发展为对文化参与的主体——生命体的关注,继而关注生物符号学,以及由生命体构成的生态符号学的研究。
评《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
陆京京(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应当来说,意义在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所以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学科,其门槛也在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中得以降低。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使得符号学研究更具包容性。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学者在扩展符号学适用领域上尤为活跃。他们由起初对文化符号学的关注,进一步发展为对文化参与的主体——生命体的关注,继而关注生物符号学,以及由生命体构成的生态符号学的研究。本书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塔尔图学者对于生命符号学相关著作的选集,学者们从多角度系统地介绍塔尔图的符号学是如何同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等人的学术遗产有机融合,其中不乏生物符号学家,文化符号学家,人类地理学家等。通过学者们思想的碰撞,知识的交流融合,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生命符号学的诸多学术观点,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推进学术进步。
本书从三个部分,层层推进,通过各位学者的著作,向读者较为全面细致辩证地展示了生命符号学之塔尔图的进路。符号域和环境界这两大理论概念,对新一代的塔尔图学者以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符号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是符号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当符号学的门槛降低到生命体有机体层次时,我们应当对符号学包容化发展感到庆幸,一方面,它能够使符号学自身得以充盈;另一方面,符号学这一研究意义的学科,也能促进生命科学,生物学以及生态学等领域的发展,在学界营造出既独立又和谐、共同进步、相互促进的良好研究氛围。
近年来,中国符号学界对于符号学的门槛,对于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研究兴趣正浓,译者对选集中学术著作的翻译,显示了译者对于该领域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该译本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符号学界对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理解研究以及自身符号学研究的发展。
一、生命符号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可能性
符号学作为一种对普遍思维规律的思索,目的就是为了理清人类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的确,在符号学发展的历史上,学者们将其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意义活动,在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展开研究。但在塔尔图学派之前,鲜有学者能将其同所有意义活动最本源的主体——生命体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能很多学术上的扩展性研究到今天这个阶段,会被很多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主动将符号学的疆域扩展到这一领域实属不易。这就好像是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你自己”,苏轼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专家学者们也很容易忽略我们人类自己作为生命体重要的一分子,在符号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扩展到整个生命体群体。符号学的研究历史,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符号都有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并且这些认识还一直处于发展之中;但直到塔尔图的符号学研究者,生命符号学才展现出其崭新的活力和十分广阔的可研究领域。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两位学者已经明确将生命体的概念及活动融入到环境界和符号域的概念上,从而使其自然而然地进入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环境界是生命体的世界,是已知的世界,它涵盖了感知和行动,是由符号关系、生命体的辨别和生命体的辨认或处理的一切所组成。符号域则更为广义,它不要求对某个特定的生命体进行聚焦,它覆盖了所有生命体。(pp. 5)
洛特曼将有机体对应到文本,将环境界对应到语境。他的创新观点就在于,他认为语境并不先存在于文本,并不是文本的前提条件;相反,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文本创造了语境,包括所有在传播行为中的参与者。(pp.13)这一观点乍一看上去,似乎像是个悖论,好像是很难被接受。但仔细思考一下,这种说法的确是不无道理的。至少,我认为文本和语境是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洛特曼这一观点的本质核心就是强调了生命体在意义活动中的主动地位。
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中,视野就一定要足够广阔。塔尔图学派的学者们显然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并没有过分地“人类中心论”,没有忽视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在符号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二、生物符号学
很显然,将符号学研究领域从对客观世界的研究转移到对人类主体的研究,是一大进步,那将其从对人类主体的研究继续扩展到其他生物的研究,更是一种突破。库尔指出,我们必须对以人类为中心的符号学中使用的模式加以更新,使其可以解释更低层次的符号过程的必然共存。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展示出符号学的重大分水岭不是在文化和自然之间,而是在生命(和生命所产生的)与非生命之间。(pp.69)再次借用上文文本的概念,文本确有边界,但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文本的边界并不在于文本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本的概念是取决于接受者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应该能意识到,符号学研究的分水岭就在于是否具有生命,所以符号学的研究很自然地一定要涉及对其他生物的研究。生物符号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将生命体的活动,或者说主体性,作为真正的、可描述的对象纳入研究范畴。这种对主体性的纳入,是根据符号过程而做出的。符号过程本身就是主体性的机制,是选择机制。(pp.88)
一谈到生物符号学,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一种不完全符号活动,即信号。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任何符号的载体,必须被感知,这点必须要坚持,但符号载体的感知者,不一定必须是一个人,可以是动物、植物以及其他有机体。这么看来,信号本身就是一个有符号载体的意义发送,且它的确是被感知。我们可以认为,但凡是生命体都可以认为是具有灵性的,都是具备感知的能力。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生物符号学也算是符号学研究的一个边界了,至少现阶段如此。
三、生态符号学——文化与自然相互影响的符号学现象
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库尔认为,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生态域与符号域其实是一致的。(pp. 127)所以很自然,将生态研究领域纳入符号研究领域是极其合理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的关注的视野就会愈发广阔,就自然会对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新的思考和解释。库尔对人们解释和影响环境的方式进行了区分,并讨论了这些解释是如何与环境问题的产生相关性的。由此,他提出了生态符号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生态学知识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和解决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某些深层的符号和文化过程的结果,和生态的、生物的过程交织在一起。对生态冲突的理解和可能的解决方式就预设了文化和生物两方面的知识,这意味着,文化符号学和生态学在这个领域内建构性地互动。(pp. 148)
当有些人还在认为文化角度的符号学和生命符号学之间有罅隙之时,生态符号学视角就提出了“自然文本”这一概念,将自然现象与其在文化文本中的翻译都囊括在其中,以此来弥合文化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之间可能存在的罅隙。
生态符号学探讨了环境和生命体的关系,就不免又将这种符号的过程看成是一种语境性的活动。生命体及其环境的互为条件性,(pp.151)环境的缺失会带来的生命体的结构变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我们对生态环境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否则,生命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必定会使人类自食其果。就比如说,生态符号学也关注了垃圾这一生态环境中给人类及其他生命体带来困扰的现象。有学者检视了洛特曼的理论,将垃圾视为一种边界现象,认为它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还指出垃圾在文化动力中存在作用,并认为符号学的定义有助于解决与垃圾相关的环境问题。从文化理论的角度而言,垃圾研究的方法来自于两个重要的理论传统,结构人类学和动力系统理论。在结构人类学的视野中,垃圾是作为对文化造成威胁、因此成为禁忌的事物类型的出现,但这一框架也承认了垃圾的积极方面,尤其是它作为文化革新来源的作用。在动力系统理论的视野中,垃圾被证明是文化动力的一个现象。这或许是迈向实际解决与垃圾和污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一步。(pp.182)当人类对于垃圾有了符号学角度上的认知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更好地处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垃圾,将其作为一种革新力量加以改造利用。
四、生命符号学的出现对翻译学界的启发
符号学将疆域扩展到生命符号学领域,这对当今翻译学的研究者一定是有所启发的。尽管很久以前,雅各布森就将翻译分成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但不可否认,一提到翻译,有些人仍然只是将其狭义地理解为两种语言的转换,这种现象在翻译研究者和译者中也不少见。如果这种思维定势成为一种常态,那对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学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其实“翻译”一词很早就在生物学领域使用。比如说,翻译是蛋白质生物合成(基因表达中的一部分,基因表达还包括转录)过程中的第二步(转录为第一步),翻译是根据遗传密码的中心法则,将成熟的信使RNA分子(由DNA通过转录而生成)中“碱基的排列顺序”(核苷酸序列)解码,并生成对应的特定氨基酸序列的过程。但不得不否认,很多翻译学研究者是不认同这种翻译同他们研究的翻译是同源的。
生物符号学界认为,在动物传播中,或者任何其他的生命系统传播中存在着符号,这提出了人类符号和其他生命体符号的可译性问题。(pp. 17)库尔指出,有不同之处,符号域才能形成,区别差异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方法。只有那种至少使用两套符码,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符号世界即符号域的一部分。(pp. 128)这种观点是否可以扩展到翻译学中?认为可译性存在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差异性,只有存在差异的两者符号系统,才有翻译的可能性。所以人类的语言符号及非语言符号和其他生命体的符号是具备可译性的条件之一。受库尔的启发,可译性的另一个条件就是人类作为解释方要有掌握两种符号系统的能力。虽然人类不能完全掌握其他生命体的符号意图意义,但人类具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对其他生命体的行为作出自己的理解。倒不妨把这种能力也当作是能掌握另一种符码的能力。
通过提出生物翻译的概念,并将人类的翻译视为语言翻译,而把环境界之间的信息交换视作生物翻译,这样做就进一步实现了对文化和自然现象的领域的联结。这种观点也会给我们一种新的思考。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认为“翻译是意义出现的过程。” (pp. 6)本书中也提到“生命过程是一个无尽的自我翻译”(pp. 77)、“任何翻译中的对象,都是符号对象。当代生物符号学观点认为,翻译是在生命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开始了的。”(pp. 83)等等。如果说一只猫一直在叫,人类将其解读为它饿了,那我们能不能说,某人将猫的叫声翻译成“我饿了”。看似有些奇怪,但并不无道理。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猫叫的信号发出者的意图,但人类的解释有足够的主观性。
生命符号学的学者们,在将符号学的门槛降低到涵盖所有生命体的同时,也提出翻译学门槛的降低,这有利于翻译学研究开辟出新的领域,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的翻译学研究者们意识到了翻译学门槛的问题,他们从符号学的角度认识翻译,对符际翻译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比如说,诗歌文本到图片的翻译,小说到电影或话剧的翻译,儿童画本中颜色的跨文化翻译,标点符号的翻译,等等。总之翻译学已经在扩大其疆域,且并得到了不错的发展。但至于门槛要降低到何种程度,仍有待学界进一步思考研究。
参考文献:
[爱沙尼亚]卡莱维 · 库尔,瑞因 · 马格纳斯 编,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汤黎等 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