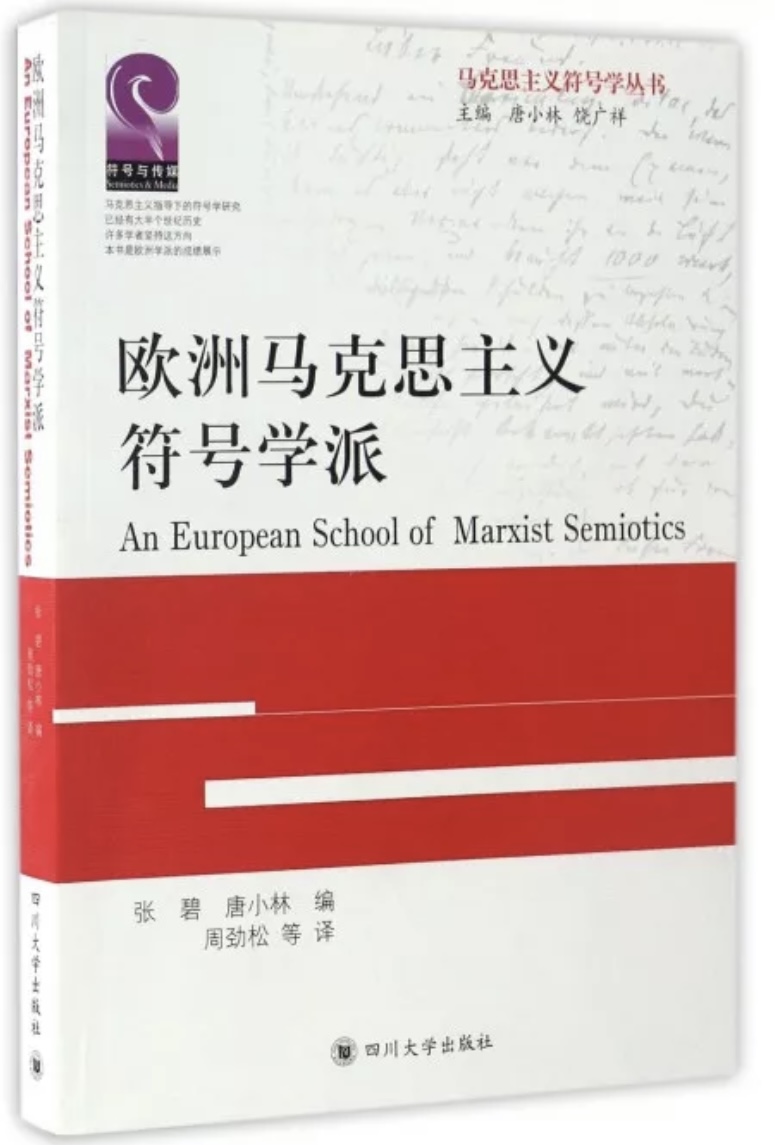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相互贯彻、互相阐释,深刻影响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理论界。由此产生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是一群“通过有意识的合作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从事符号研究及其与价值、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及研究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互证的学者。他们关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符号研究,同时关注符号研究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高度符号化的时代里,用最具现实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处理符号问题,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自然就成为我们思考时代问题之前需要研读、批判的对象。
李智鑫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相互贯彻、互相阐释,深刻影响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理论界。由此产生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是一群“通过有意识的合作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从事符号研究及其与价值、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及研究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互证的学者。他们关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符号研究,同时关注符号研究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高度符号化的时代里,用最具现实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处理符号问题,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自然就成为我们思考时代问题之前需要研读、批判的对象。
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国,一批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符号学掀起高潮之时,就敏锐地捕捉到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这一发展趋势。1993年《哲学研究》刊登了章建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符号概念》一文,把符号学视作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公分母、方法论,希望由此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增长点。该文基本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成果,极具理论前瞻性和革新意义。2000年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关注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的代表者,收集整理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文献,打开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视野,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阿尔都塞理论的符号学再审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符号化》、《符号学视域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学术成果。另外,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为拓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作了一系列努力:2016年起推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翻译出版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者的文论著作,整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的知识谱系,提出了“回到经济基础,回到商品分析,回到社会关系,回到未来朝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构想,夯实学术基础并力图摸索高度符号化时代的文学道路。
笔者阅读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正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系列之一。该书包括14篇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代表人物的译作,其中第一篇译作是苏珊·佩特里利所著《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系统地介绍了几位代表人物的学术研究及笔者与之交往的大致情形:波兰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33-2006)、意大利费鲁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 1921-1985)、奥地利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 1943-2010)、意大利奥古斯托·庞齐奥(Augosto Ponzio, 1942)。全书以“引论部分”为大纲,主体部分设置四个专辑,每一专辑涵盖三篇译文,总计12篇。每一辑介绍一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学者的生平经历、学术著作及主要观点。书末还有一篇保罗·科卜利所著《讨论:符号伦理学、意志论、反人本论》,简要回顾了皮尔斯符号学是如何逐步取代索绪尔符号学的,并反思了早期符号伦理学存在的意志论缺陷并提出反人本论的必要性,最后展望了符号伦理学工作在21世纪的施展领域。为了更好地读懂符号学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彼此阐发理解,笔者认为有必要重点回顾“亚当·沙夫专辑”。
亚当·沙夫(1933-2006)一生著作颇丰,包括《语义学导论》(1962)、《历史与真理》(1971)、《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8)、《马克思主义引论》(1947)、《人本主义、语言哲学和知识理论》(1975)等等,笔者自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讨论沙夫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只能回顾沙夫思想中涉及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关联的部分。作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致力于用符号学参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解决问题。例如沙夫在上世纪80年代用符号学分析和比较了以不同语言出现的不同样式的 1975 年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用。
与马克思批判“商品拜物教”(fetishism of commodities)相对应,沙夫批判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生物学家埃里克·H.伦尼伯格(Eric H. Lenneberg)提出的语言阐释,认为语言不应当作人类天性或非自然性,语言应该被归纳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而且是形成意义的材料。沙夫进而提醒警惕“符号拜物教”(fetishism of signs)概念,符号关系应当是使用和生产符号的人之间的特定社会条件关系,而不是符号与意义之间的锁合关系。沙夫之所以强调警惕“符号拜物教”,因为语词符号的解释关联着社会意识形态,能够造成对社会群体利益的主观干扰。同时,人类非语词交流活动与语词交流活动等量齐观,进而我们可以得出科学主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意识形态的结论。
沙夫将晚年生命全身心奉献给了人类个体、社会以及社会运动问题的研究。《人的哲学》(1961)、《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982)记录着沙夫对结构性失业、移民和作为工作-商品来理解的“自由劳动”的终结。沙夫提出当下欧洲社会政治的四个病症:核战的危险、生态灾难的威胁、人口爆炸、“结构性失业”,当下时代反观其思想,是有预见性和忧患意识的。沙夫看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激进的、积极的人本主义。当反马克思主义者质疑马克思忽视人的个体价值、个人价值不应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被忽视时,沙夫坚定地认为“人本主义”这一语词的歧义性导致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沙夫与阿尔都塞之间的论辩记录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的方法》中,沙夫运用符号学(或称语义学)对符号(人本主义)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坚持认为不在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特定个体谈论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是荒谬的。
沙夫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语言哲学、符号学、知识理论还是晚年所致力的政治经济学,贯彻的是坚持将人类完全视作广义符号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立场。符号的解释项是无限衍义的,如同语言需要在人际交往中发展,离不开对人类具体处境的关注。沙夫从人本主义出发探究符号,再由符号回到对人本主义的关注,包含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人性关怀。由沙夫的思想,我们进而读到罗西-兰迪、伯纳德、庞齐奥的思想,可以发现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是简单机械地理论叠加,符号学无疑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适用域,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也能够帮助符号学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上,让符号无限衍义,获得更广阔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唐小林、张碧主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章建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符号概念》,《哲学研究》1993(03)
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2(02)
张碧:《阿尔都塞理论的符号学再审视》,《南京社会科学》.2014,(01)
毕芙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符号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04)
毕芙蓉:《符号学视域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06)
唐小林、饶广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央级》,2017(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