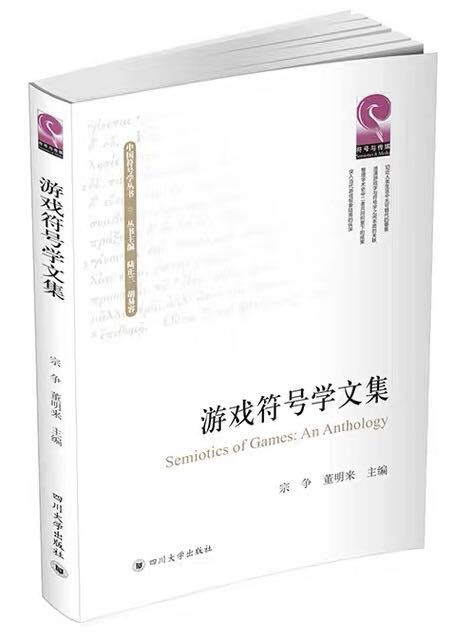
在电子游戏被声讨为“精神鸦片”的喧嚣声中,讨论“游戏研究”可能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电子游戏(泛指数字游戏、电脑游戏、网络游戏等)已经成为当今主流的娱乐模式,释放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学术界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对它熟视无睹。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游戏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语法学(游戏规则)、语义学(虚拟世界)、语用学(玩家活动)。这三个维度也基本是《游戏符号学文集》潜在的组织依据,支撑着文集的三大模块:理论研究、叙事研究、文化研究。
张新军评宗争、董明来编《游戏符号学文集》
张新军
在电子游戏被声讨为“精神鸦片”的喧嚣声中,讨论“游戏研究”可能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电子游戏(泛指数字游戏、电脑游戏、网络游戏等)已经成为当今主流的娱乐模式,释放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学术界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对它熟视无睹。
先说几个自己认为的标志性事件:
1998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召开第一届“数字游戏与文化”研讨会,也开启了“游戏学派”与“叙事学派”争鸣的序幕。
1999年,贡扎拉·弗拉斯卡(Gonzala Frasca)在其文章“游戏学遭遇叙事学:(电子)游戏和叙事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中创造了“游戏学”(ludology)一词,指尚不存在的研究普通游戏(尤其电子游戏)及游戏活动的学科。对于游戏研究的学科身份而言,这个词造的很妙,一是词尾自带学科标记,二是其他可选的词汇不多,game theory特指博弈论,就只剩下game studies了。
2001年,网络学刊《游戏研究》(game studies)创刊,游戏理论家艾斯本·阿尔瑟斯(Espen Aarseth)将这一年被称作“电脑游戏研究元年”。
2003年,《自然》杂志发表Shawn Green & Daphne Bavelier的研究“动作类电子游戏改进视觉选择性注意力”,表示电子游戏对智力有提升作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011年,美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正式承认电子为一种艺术形式(参见Pearce 2014)。
2017年,美国艺术基金会和美国人文基金会资助的《瓦尔登湖:一款游戏》在多个平台发布,同年还发布了该游戏的课堂教学指南。这是基于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同名作品而制作的一款仿真探索叙事类游戏,获奖无数,好评如潮(参见Wolf 2021)。
游戏乃人类和动物共有的一种活动,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成为严肃的人文学术研究对象。具体到电子游戏,在技术领域和教育领域(包括心理学)一直都是研究热点,正统性与合法性似乎不言而喻,尴尬的是文艺与传播领域。过去二十多年,中外学者都在寻求在人文领地中确立游戏研究的学科身份。《游戏符号学文集》汇集了国内学者的文章,用编者的话说,“在缺少学界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一批学者(大部分是年青人)正在这条路上踽踽独行。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却十分顽强,这是我们编纂本书的初衷——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2)。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游戏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语法学(游戏规则)、语义学(虚拟世界)、语用学(玩家活动)。这三个维度也基本是《游戏符号学文集》潜在的组织依据,支撑着文集的三大模块:理论研究、叙事研究、文化研究。
一、游戏理论问题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或领域,游戏研究的理论建构面临着天然的窘境:(1)理论遗产屈指可数。能够想起的大概不过是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凯罗伊斯《人、玩、游戏》、以及哲学话语中关于游戏的零星论述(如维特根斯坦),这些资源具体对电子游戏有多少启发还有待商榷。(2)研究对象充满争议。游戏研究的核心关注其实是电子游戏,在建立学科正统性上举步维艰。因此,一开始,挪用文艺理论、艺术美学等学科资源几乎成了本能的、唯一的选择。
文集的理论板块有5篇文章。首先是吴玲玲的背景性文章,“从文学理论到游戏学、艺术哲学——欧美国家电子游戏审美研究历程综述”,追踪了西方国家中游戏学兴起的学术语境、发展历程、方法进路、以及艺术诉求。
第二组文章聚焦研究对象,从符号学视角刻画游戏的文本特征。董明来“游玩与阅读——游戏符号学初探”区分“被游玩的游戏”和“被观看的游戏”,通过游玩和阅读之类比来描述被玩的游戏的文本性。宗争“游戏的符号学基础——‘游戏文本’与‘游戏表意’问题探索”旨在厘清游戏学的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四个层面:游玩事实、游戏文本、游戏内文本、游戏元文本,提出游戏文本自身很难表意,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向度,但提供了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项”。白承国、赵永升“游戏的文化符号学研究”以索绪尔符号学来刻画游戏的符号系统与设计原则,重点探讨了以“叙事程序”诱导玩家互动的游戏体验。
从家族相似性的观点看,相对于文学艺术,体育似乎才更像是游戏的典型范例。魏伟“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述评”追踪了巴尔特、波德里亚、布尔迪厄、艾柯的体育符号学思想,描绘了国内外的新近发展态势,表达了建立体育符号学的学科诉求。
对其他学科理论的资源挪用,游戏研究表现出欲拒还迎的态度。游戏学要建立自己的本体理论、独立的学科身份,一味地比附已有的经典艺术形式注定是要走向死胡同。游戏,尤其饱受争议的数字游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文化或技术制品,必须开发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实践方法,才能处理电子游戏无与伦比的独特范畴。初步来看,游戏研究采取符号学进路会更有效能,这是因为电子游戏的特异之处在其符号结构与表意方式。就艺术界面而言,虽然电子游戏的表征能力异常强大,但并不能说就完全超越了电影画面或虚拟博物馆。正是其符号学机制使得游戏体验完全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审美经验。
二、游戏叙事问题
游戏学的理论窘境使得这个新领地很容易被已有的学术部落入侵和殖民,主要有文学理论和电影理论,尤其是贯穿二者的叙事学。于是,在游戏研究这片新发现的边疆地区,一开始就爆发了游戏学与叙事学的争执。游戏学阵营主要有阿尔瑟斯、弗拉斯卡、杰斯珀·尤尔(Jesper Juul)、埃斯科里宁(Markku Eskelinen)等。叙事学阵营则是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布伦达·劳雷尔(Brenda Laurel)、珍妮特·默里(Janet H. Murray)、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游戏符号学文集》所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国内学者的态度。
首先,文集提供了弗拉斯卡和尤尔文章的汉译版,呈现了游戏学派的立场。弗拉斯卡“拟真还是叙述:游戏学导论”敏锐地抓住了游戏和叙事在符号机制上的本质差异:叙事是基于表征(representation),而电子游戏不仅是基于表征,更是基于仿真(simulation)。尤尔“游戏讲故事?”从媒介生态、时间性、互动型三个方面重申了电脑游戏和叙事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与排异。
接下来的一组文章集中讨论数字媒介的叙事问题。张新军“故事与游戏:走向数字叙事学”提出数字叙事学的核心是叙事性与互动性的关系问题,认为叙事学既要尊重电子游戏的特殊性,又要通过叙事来提升数字媒介的艺术潜力。甘锋、李坤“从文本分析到过程研究:数字叙事理论的生产与流变”同样提出,数字叙事理论面临的是“叙事”与“交互”两个概念之间的冲突,评述了蒙特福特、霍伊尼采等人的解决方案。程丽蓉“跨媒体叙事对符号叙述学理论的挑战”探讨了跨越不同媒介平台的叙事增殖问题,也就是詹金斯(2006)所谓的“跨媒介故事讲述”(transmedia storytelling)。
最后两篇分别探讨游戏学的理论基础和电子游戏的艺术地位。宗争“游戏(与体育)的广义叙述学理论基础”以游戏文本的双重互动来刻画游戏叙述文本,作为建立普适性游戏理论的出发点。苏世昌“兼容传统与后现代:论电子游戏艺术性的确立”从传统艺术和后现代艺术两个方面为电子游戏的艺术性进行了辩护。
关于游戏与叙事的争执问题,首先需要抛开学科囿见,澄清叙事学何以会干预游戏研究。从劳雷尔的《作为剧院的计算机》(1991)和默里的《全息甲板上的哈姆雷特》(1997),到梅多斯《暂停与效果:互动叙事的艺术》(2003)、瑞安(2015)设想的“总体艺术”,叙事学派追求的是所谓的新媒介“圣杯”——虚拟现实中的互动叙事。游戏当然不是叙事,但是,叙事为游戏提供了一种意义模式,一种审美品质的来源,至少目前是软件工程师们偏爱的思路。
三、游戏文化研究
这一部分文章侧重游戏的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心理等更广泛的视角。
第一组文章集中于“游戏化”(gamification)在传播语境中的机制与功能。蒋晓丽、贾瑞琪“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游戏话及其表征——一种符号学视角”指出,传播的游戏化实际上是将游戏化的思维与理念运用于传播活动,充分发挥参与性与创造性,真正发挥传播作用的有益路径,探讨了游戏化传播的基础、实践、效果。孟伟“电子游戏中的互动传播——游戏中的游戏者分析”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游戏者与游戏内容之间的互动:角色扮演、互动语境、交互叙事。李俊欣“符号叙述学视角下的新闻游戏及其伦理反思”将新闻游戏视为纪实叙述与游戏虚构的杂交,认为貌似提供了开放与互动的形式,但是读者在选择和判断上反而更加被动。
第二组文章聚焦游戏玩家。诸葛达维“游戏社群情感团结与文化认同的动机机制研究”通过民族志观察发现,游戏社群的形成与运行遵循互动仪式的情感传播机制。关萍萍“试论网络游戏玩家的‘游戏内传播’:格雷马斯方阵视角下的游戏价值论”,采用格雷马斯方阵对网络游戏及其玩家自我传播行为进行分析,发现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所寻求的“价值”所在。宗争“游戏‘沉迷’的文化符号学解读”以游戏中的身份为线索,对游戏成瘾提供了一种符号学说明。
最后是游戏文化层面的具体话题。吴玲玲“电子游戏审美研究的困境与游戏诗学的建构”通过对电子游戏的文本描述,建议从形式、类型、文化、精神分析四个侧面来建构游戏诗学。宗争“射何以成道——游戏文化机制的符号学研究”解析了射箭活动的各个层面及衍生活动,从符号学视角描述了其游戏文化机制。任文、魏伟“奇观体育与体育奇观:罗兰·巴尔特的符号体育观”
四、余论
(一)电子游戏的艺术地位
中外学者均有大量的文章来为电子游戏的艺术地位进行辩护,往往旁征博引,尤其喜欢引证后结构、后现代理论。一方面,数字文本性确实有契合这些大理论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多少有一种狐假虎威的感觉,无意中沦为这些理论的注脚。电子游戏是否一门艺术形式,这本是个伪命题。想想柏拉图对诗歌的斥责,想想当初对电影的藐视。再如京剧,今天视之为国粹,但想想一百多年前泡戏园子的情景,嗑着瓜子品着茶,甩着毛巾叫着好,哪里像高大上的艺术?
说到底,艺术地位的根基是有一个公认的经典系统(canon),那么,目前电子游戏有自己的《哈姆雷特》或《霸王别姬》吗?遗憾的是,稍具艺术品质的电子游戏,都是知识精英的自娱自乐,沦为游离于产业之外的“独立游戏”或“艺术游戏”(Pearce 2014)。这种小众化与游戏产业大众化的鸿沟构成了瑞安所谓的数字文本性的分裂状况。瑞安开出的药方是理论先行,具体就是通过向游戏文本注入叙事性来提升其艺术性。
话又说回来,这种艺术小众与娱乐大众的分裂状况,并不仅仅存在于电子游戏领域,文学、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领域哪个不是如此?只不过这些艺术领域已经见怪不怪、心态平和,毕竟它们拥有各自的、历史沉淀的“伟大传统”。如此可以看到,游戏研究的学科焦虑未必是理论资源的贫瘠,而是经典作品的匮乏。
(二)游戏研究的学科地位
伯纳德·佩伦和马克·沃尔夫先后编辑出版多本游戏研究文集。如果说他们的《电子游戏理论读本》(2003)还在为电子游戏研究的学术正统性进行辩护,那么《电子游戏理论读本2》(2009)则干脆宣称,“毫无疑问,电子游戏研究已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自己的身份”(5)。按照两位编者的说法,电子游戏研究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开始明确自己的性质与范围,编制工具与术语,把研究发现组织成一个连贯的学科。二人合编的《劳特利奇电子游戏研究指南》(2014)则呈现了更广泛的跨学科视角,如技术、形式、社会、文化、哲学等领域。
阿尔瑟斯一贯主张游戏学的独立学科身份,但也承认不可能只有一个游戏研究领域,有人工智能、社会学、教育学等许多研究方向。为此,他提出游戏研究的三个维度及其相应的研究视角(2003):(1)游戏活动(游戏者的行动、策略、动机),对应社会学、民族志学、心理学等视角;(2)游戏结构(游戏的规则,包括仿真规则),对应游戏设计、商务、法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视角;(3)游戏世界(虚构内容、类型/层次设计、风格等),对应艺术、美学、历史、文化/媒介研究、经济学等视角。
(三)优先事项是游戏批评
游戏研究有一种冲动,想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完整的理论框架,这并不是理论先行的要旨。理论先行的意图在于,让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积极干预游戏创作,以生产出既有审美品质和思想深度,又能获得大众玩家广泛推崇的游戏作品。这个目标值得追求,非常宏大。但是,也可以换个思路,批评先行是否更加现实一些?如果承认电子游戏艺术性和学科性的基础是经典化,那么基础的基础是开展游戏批评,也就是对具体的游戏文本进行美学、认知、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析评论。游戏批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各种游戏进行类型学描述,也就是说,游戏学需要自己的文类(genre)体系。针对具体文本的游戏批评工作,国外做的比较多一些,教育学领域比较多一些。
马修·萨瑟恩(Matthew Southern)认为,电子游戏所产生的道德恐慌,与意识形态或日常生活的政治密切相关,被用来为增加管制权力做辩护。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统治集团的权力不能仅仅通过强制来维持,而且还必须争取民众的同意,因此通俗文化在获得赞同方面起关键作用,是散播思想和原则的一个意识形态武器。电子游戏和全球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些类型游戏的媒介内容看出。萨瑟恩以战争主题的游戏为例,说明媒介新闻、游戏产业、好莱坞电影之间纠缠不清的表征关系。如伊拉克战争的现实性与所人们看到的影像表征之间很少有联系。战争中丧失的人性、新闻中迷失的事实,也同样在游戏的媒介内容中消散无形。电子游戏沉醉于高精端武器,却抹掉了现实冲突中的平民伤亡。游戏叙事里的战争狂人可能模仿现实(如萨达姆),但却将现实中复杂的跨文化权力关系简化成“善恶”对立(现实中也有所谓邪恶轴心论)。
此外,电子游戏还服务于男权文化的再生产。虽说也开发诸多女性游戏(如着装、化妆类),但都像“芭比”娃娃一样潜在地将女孩塑造成霸权文化所预期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她们沦为文化消费的欲望客体。
但这还仅仅是“媒介内容”的表征政治学,更重要的应该是仿真的政治学,也正是电子游戏抵抗社会霸权的基础之所在。虽说游戏程序也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但却比传统文本更能显示自己的建构性,因此根本上解构性的。特德·弗里德曼(Ted Friedman)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更适合成为一款概念游戏而不是一部好莱坞电影,意思是《资本论》更适合仿真艺术而不是表征艺术。从表征到仿真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走向巴赫金的社会实践论。
参考文献:
Aarseth, Espen. “Computer Game Studies, Year One,” Game Studies 1.1 (2001). <http://www.gamestudies.org/0101/editorial.html>
Aarseth, Espen. “Playing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DAC 2003. Melbourne: RMIT University. <http://hypertext.rmit.edu.au/dac/papers/Aarseth.pdf>
Green, C., & Bavelier, D. “Action video game modifies visual selective attention,” Nature 423 (2003). 534–537.
Frasca, Gonzalo. “Ludology meets narratology: Similitud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video)games and narrative.” Helsinki, 1999. <http://www.ludolgy.org.>
Friedman, Ted. “Making Sense of Software,” in S. G. Jones (ed.), CyberSociety.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pp. 73-89.
Jenkins, Henry. Convergence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Pearce, Celia. “In dependent and Art Games,” Ryan, Emerson, & Robertson (eds.) 273-277.
Perron, Bernard, & Mark J. P. Wolf (eds). The Video Game Theory Reader 2.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Ryan, Marie-Laure. 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2: Revisiting Immers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Litera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Ryan, Marie-Laure, Lori Emerson, & Benjamin J. Robertson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Digital Med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Southern, Matthew. “The Cultural Study of Games: More Than Just Games.” www.igda.org/articles/msouthern_culture.php
Wolf, Mark J. P. (ed). Encyclopedia of Video Games, 2nd ed.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2021.
Wolf, Mark J. P. & Bernard Perron (eds). The Video Game The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Wolf, Mark J. P. & Bernard Perron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Video Gam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宗争,董明来编. 《游戏符号学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