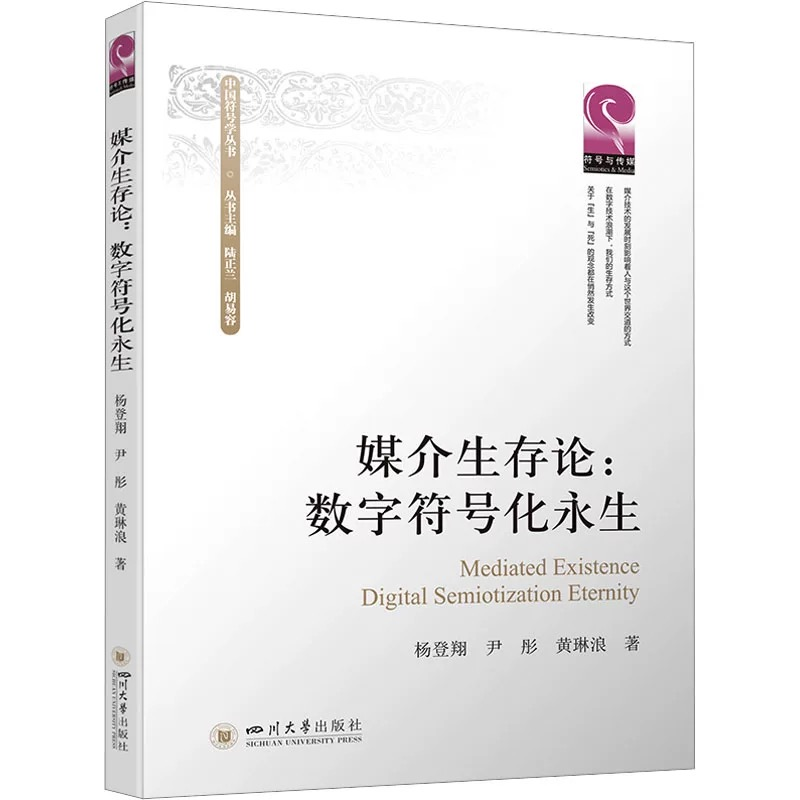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媒介”是连接人类与世界的桥梁,又是形塑人类生存方式的隐性框架。
王苑郦评杨登翔、尹彤、黄琳浪 《媒介生存论:数字符号化永生》
王苑郦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媒介”是连接人类与世界的桥梁,又是形塑人类生存方式的隐性框架。本书第一章从“媒介”概念出发,剖析其在古今、中外不同语境中的多重意涵。在此基础上,第二章以麦克卢汉的媒介关系论为切入点,揭示媒介如何通过改变人类感知的尺度,深刻影响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第三章聚焦媒介技术与人类身体的关系,探讨身体如何作为媒介的基础节点,以及技术如何重塑身体与媒介的互动。第四章引入“具身性”这一视角,分析不同媒介技术时代的具身性演变,并探讨“赛博格”思想对人类主体性的挑战。第五章则转向媒介化生存的极端形式,探讨肉身死亡后,人类如何通过媒介实现“永久在场”。最后,第六章聚焦数字符号化永生的技术构想,揭示其在认知哲学与伦理学层面引发的深层争议。
第一章 重访“媒介”概念
目前,学界对于“媒介”的理解仍处于亟待厘清的状态,一方面,媒介技术的革新速度快到让所有人应接不暇,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媒介融合”更加剧了理解媒介的困难。在前传播学语境中,“媒”泛指人、事、物之间广泛的连接,而“介”的出现较之“媒”更早一些,有区隔之意,在行文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媒介”在传统语境中有着相当丰富的意涵。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无论是“媒介”还是“Media”,都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前,这对概念都已经广泛存在于中西文化之中。而当下,媒介的关系论和载具论是学界主要的两种观点,此二者常常被讨论者树为对立姿态,然而这两种观念并非不可调和,就像语言的每一次使用,都受其组织结构的约束,语言的发生也即是这种信息显现的过程,二者是一体的。同样的,广义上的媒介本身的组织结构就已经携带了信息,这些信息约束、形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
第二章 媒介与人的生存
作者选择以麦克卢汉的理论为代表剖析媒介的关系论,探究媒介的影响力。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尺度”,由此带给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新途径。“媒介关系论”极大拓展了媒介研究的视域,却又使得定义过于宽泛。一些研究急迫地将传统媒介之外的事物置于“媒介”范畴展开分析,然而对于何者为“媒介”却缺乏判断标准。在思维层面,之所以要将“媒介”问题置于讨论人类文化社会的核心,是因为人类的认识活动经由媒介才能实现,而媒介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对象感知的角度、方式,进而影响我们的意义生成。在实践层面,一切的人造物都在实践中参与了我们意义世界的生成、参与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改造。
第三章 媒介发展与“身体”的嬗变
过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媒介技术中一直沉默着的最基础的存在——人的身体,身体既是人与环境互动最基础的媒介,又是一切外部技术物的节点。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赋予灵魂崇高地位,又将肉身摆在较低的层次之中,而现代哲学出现了抑心尊身的趋势,意识主体和理性主体遭到严厉批判。法国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梅洛-庞蒂认为真正的身体应该是指肉身与心灵以运动机能动态结合起来的产物,缺少心灵的肉身就是行尸走肉,由此,身体逐渐从笛卡尔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摆脱出来。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的认知就是身体的认知,当个体缺失身体以后,那么认知与心智则不复存在。身体是具身的源泉,从身体到具身,实际上是一个将身体从对象变为“状态”的悬置过程。在传统媒介时代,媒介技术主要通过扩展身体的感知能力来发挥作用。例如,语言作为最早的媒介,通过听觉和视觉文字扩展了人类的交流能力;印刷媒介通过视觉感知的强化,重塑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使知识的传播更加广泛和系统化。然而,随着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兴起,媒介技术不再仅仅是身体功能的延伸,而是逐渐成为身体感知的重塑者。电子媒介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即时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人类的感知方式从单一的感官体验转向多感官的综合体验。数字媒介和虚拟现实技术则进一步模糊了身体与媒介的界限,通过沉浸式体验让人类的身体感知超越了物理世界的限制。
梅洛-庞蒂的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是人类感知和认知的基础,而媒介技术通过改变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方式,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感知结构。例如,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使人类的身体逐渐成为媒介化的节点,身体的感知和行为被技术所中介化。这种中介化不仅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还对人类的主体性提出了挑战。当媒介技术逐渐渗透到身体的每一个感官和行为中,人类是否还能保持对自身主体性的掌控?
此外,媒介技术的发展还带来了身体的异化问题。随着赛博格和数字永生等技术构想的出现,人类的身体逐渐被技术所替代和重构。例如,全息影像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得逝者的信息可以被永久存储和传播,模糊了生者与逝者的界限。这种媒介化生存虽然延长了主体的存在感,但也引发了关于人类主体性与伦理的深刻争议。当人类的身体被技术所中介化,甚至被技术所取代时,人类的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是否会被重新定义?
第四章 媒介具身性的二元划分及其演变
作者以“在场性”和“体验性”为标准建立媒介技术具身性的二元划分,并据此对不同媒介技术时代中的具身性演变情况展开论述。从前语言到如今的新媒体时代,人类依旧不断想要超越自身在物质身体与思想智能上的局限性,媒介环境由人与机器共同塑造,“赛博格”思想不断发展。电子传播时代媒介技术的进步逐渐实现了虚拟在场对生理机制的束缚的突破,具身性效果逐渐与实在在场的效果等同,越来越全面地完成对主体感知觉比例的协调。同时,赛博格的出现对人的定义提出了挑战,人未来的生存状态或可被总结为两种,一种是指身体与机器共存的生存状态,另一种则较为极端,即人的肉体被彻底抛弃,心智被截除为最终的延伸符号进入赛博格空间,实现灵魂的“永生”。然而,当人们被赤裸裸地投放到电脑和手机屏幕中,就犹如处在全景敞视的监狱之中,永远处于媒介的囚禁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人的主体性危机,在未来社会,人类不得不面临着“人类的自我价值在何处”的问题,在面对不断更迭的技术,“媒介焦虑”是引发主体性危机的一大源泉,当对于社交网络的需求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人类很可能成为一个个数据节点,最终沦为技术的奴隶。
第五章 肉体之外:逝者的媒介化生存
随着各种媒介技术的发展,肉身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主体存在的终结,即使逝者在生活中已经缺席,但其生前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也存在被继续传播的可能,从而使逝者在媒介上实现永久在场。部分学者提出“媒介化生存”的概念,以此揭示人们不仅使用媒介,还生存在媒介中的事实。例如,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使人类的身体逐渐成为媒介化的节点,身体的感知和行为被技术所中介化。随着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渗入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人与媒介的界限日益模糊,人自身也成为了媒介化的产物,媒介化模糊了在场与缺席的界限,媒介成为了连接生者与逝者的中介空间。首先呈现的形态是以网络哀悼为主的承载集体记忆的纪念网站,用虚拟的符号叙事代替身体实践;全息影像的出现使得生者与逝者同台成为可能;Kuyada的AI机器人可以创造、甚至复制出一个数字人格,复刻出一个新的自我。有学者指出,媒介化生存的主体是一种新型的人,也被称为赛博格人,与此同时,新一轮人类文明革命也随之而来。
第六章 数字符号化永生的可能及其反思
数字符号化永生作为后人类主义的技术构想,正在引发认知哲学与伦理学的深层争议。该命题试图通过脑机接口、神经信息映射与算法建模等技术手段,将人类意识转化为可存储、可传输的数字符号系统,进而实现脱离肉体的意识“永远在场”。梅洛-庞蒂的具身认知理论强调意识始终根植于肉身化的在世存在,数字载体对神经脉冲的符号化转译,实质上将不可还原的具身经验抽象为离散数据流,导致意识主体性从生存论层面的断裂。更严峻的伦理挑战在于,数字永生可能重构人类的存在论等级——拥有无限迭代能力的数字意识将形成新的认知特权阶层,而生物人类则沦为技术进化链上的次级存在。这种技术愿景折射出的,实质是资本逻辑对死亡禁忌的祛魅,通过制造“可计算的不朽”幻象,完成对人类死亡焦虑的商品化收编。
技术本身无善恶之分,但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工具理性的膨胀可能导致人文价值被遮蔽,媒介逐渐异化为操控主体认知的装置。唯有在承认技术具身性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通过建构人机共生的主体间性伦理,方能在符号化永生与生物有限性之间确立辩证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