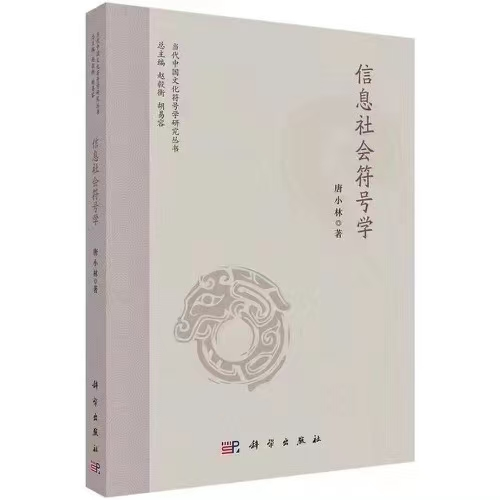
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的生活以及发生中的世界?我们是否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困境?我们又该对自己作出何种解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人以不同的方式、角度尝试着回答,稀松平常抑或振聋发聩,而我们,阅读、感受或怀念。但那些分不清是真实还是被建构的晦暗的时代抑或“黄金时代”早已不在,面对着周遭的巨变,我们必须给出我们自己的回答。
陈世杰评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
陈世杰
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的生活以及发生中的世界?我们是否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困境?我们又该对自己作出何种解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人以不同的方式、角度尝试着回答,稀松平常抑或振聋发聩,而我们,阅读、感受或怀念。但那些分不清是真实还是被建构的晦暗的时代抑或“黄金时代”早已不在,面对着周遭的巨变,我们必须给出我们自己的回答。在此,《信息社会符号学》即是这样一种尝试,作者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并呈现了他关于信息社会的基本构想与观点,立足过去、现在,朝向未来,为我们理解我们当下的生活和世界作出了符号学式的解释努力。
一、信息社会的符号本体论
“世界的本体是符号”,是作者在导论中量明的第一个观点,也是整本书的理论基础。符号学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行于世间,更可以成为一种本体论视角,用以观照我们的生活世界本身。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作者将世界的符号构成分为“前景”与“背景”两部分,只有前景才是人类的意识可以触碰到的、才是包含着自然的符号化过程的符号世界。于是进一步,社会的变迁实际就是符号的变迁,信息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意义建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作者在导论为我们明确了社会符号学与符号社会学的分野,社会符号学即对社会意义建构方式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将整个社会当作一个符号系统来研究。作者亦沿着这条进路,将整个信息社会当作一个大局面的文本,来“重点考察作为符号活动的信息行为及其互动,以及所产生的差异性结果和文化后果”。于是,在从符号学的视阈厘清信息和信息社会两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信息社会的三幅面相:媒介面相、智能面相与消费面相,认为“信息社会就是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和消费社会的三位一体”。进一步,在皮尔斯符号三元论意义上,将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和消费社会分别对应于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符号文本的再现体、对象、解释项,提出“媒介、智能和消费分别充当了信息社会意义建构的表意机制、生产机制和动力机制,完整的信息社会符号学应该就这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在此,作者建立在信息社会符号本体论基础上的形式理论版图已全部浮现。
二、信息社会的意义建构方式
在完成对信息社会的总括后,作者开始深入信息社会的每个面相,以探索信息社会的意义建构方式。首先,作者注意到“连接”这一人类最初的存在方式、接触行为与文化符号,在以媒介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口语-身体媒介时代、文字-书写媒介时代与数字-网络媒介时代后,人类社会的连接方式也经历了强连接、弱连接到超连接的转变,这也导致了社会意义建构方式的变迁。“数字-网络媒介时代的无距连接,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其对人类的影响之深远,也许再怎么说都不足为过”,当超连接成为信息社会的文化主型,连接不仅为意义奠基:“我”在移动互联网存在,“我”就存在于世界中;连接还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权力,成为意义、话语或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当然,文化是社会表意活动的总集合,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超连接一旦超出需要而产生过度连接,可能导致的是弱关系、弱理性与弱文化。
其次,作者从符号叙述体裁的角度,为我们展示出信息社会的“表演性逻辑”:信息社会作为大局面符号文本具有拟演示的体裁偏向。作者将叙述体裁划分与社会形态相关联,认为存在演示和记录两种基本社会形态,在采用以媒介划分的社会形态基础上,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演示、记录、拟演示的演进历程,并援引巴赫金、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符号互动学派、哈贝马斯等理论家的理论资源,论证了人类符号行为的演示性质,并指出:“以移动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社会是空间主导的社会,它不断构筑以言演事的平台,来达成人类的各种演示类叙述行为,并由于前台与后台的反转,改变了社会的表意结构及其伦理关系“。
然后,作者从新媒介的特点出发,探讨了信息社会的文化景观:媒介自指导致诗性符号的大量涌现。新媒介社会是万物皆媒的社会,万物皆媒导致媒介自指,媒介自指即符号自指,带来的是生活世界的诗意化。而诗性符号指的是超出实用意义的人造符号,在数字-网络媒介时代以景观的方式呈现,但这一现象并不是符号的突变,“实际上整个20世纪的话语领域和生活世界都在为此做准备,或者说在发生某种诗性转折”。作者借助广义叙述学中的“双层区隔”理论,指出诗兴符号景观是由双层框架即文本框架和标示框架搭建而成:“双层框架原则,导致了诗性符号的批量生产,这是数字-网络媒介时代诗性符号景观过剩的原因,也是其生产机制”。最后,作者借助“意义生态”的概念,认为:“信息社会诗兴符号的独大,带来的并非是诗性生活、诗意栖居,而是意义生态的失衡”。
接着,作者在指出诗兴符号景观的生产机制是双层框架原则后,又进一步提出“装框”这一信息社会的普遍意义生产方式。作者先是论述了信息这一事物除了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属性外,还拥有一个特殊的时间价值属性,而与用时间消灭空间不同,信息革命用时间消灭了空间本身,而“被时间消灭的空间的信息要存在,就必须重建空间,而装框就是重建空间的方式”。装框便是给失去了空间的信息单位重建或重构新的空间,使之成为新的事物,而装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作用,与其编码/解码、认知/建构、交流/传播的功能有关,装框虽然成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意义生产方式,但也同样带来新的阶级分野与社会不公。
随后,作者围绕“人的意识能否符号化”这一根本问题,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考察了智能社会的意义生产机制,即智能获取与解释意义的能力,提出人工智能便是重建“元意识”。人工智能主要有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种类型,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三条进路,以及被动和自由两种符号主体,而人工智能获取意义的途径则有遗传性、学习性和意向性三种。在对自由主体何以可能以及意向性的论述中,作者指出:“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的全部努力,只不过是实现了对人类本能的模拟”。但作者又提出:为何人工智能一定要按照人类智能的方式来实现?一种超级人工智能的设想是可能的,而当超级人工智能真正实现,建立了自由的符号主体,人类可能将面临这样的后果:人的离场、意义的消失和人类历史的终结。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从数字化时代的整个符号格局变动的层面考察了网络意义的生成方式,数字化生存即元时代的开启。元符号即关于符号的符号,作者指出人类社会依次完成了从物-符号到纯符号再到元符号的三级跳,而在元时代的当下,信息社会形成了物符号、纯符号和元符号的倒三角关系,物性越来越弱,符号性越来越强,信息社会即元符号主导的社会。而进一步,从文本层面考察数字社会,其存在物理现实文本、虚拟现实文本和交互现实文本三重文本形态,并借助跨文本运动来生成意义。作者指出:“不同文本间的跨层运动导致数字时代意义生成的极度复杂,所带来解释困难、解释漩涡,也必然给信息社会带来诸多问题”。
三、信息社会的意义主体与人类生活
作者对信息社会做了相当形式化的考察与理论推断,这不仅依赖于符号学、哲学、媒介学等理论资源或方法,更在于将信息社会本身就当作符号来对待。作者在导论部分对世界的符号构成的描述,显示出强烈的人类主体性:“一切人类活动所触及的自然之物,均化身符号,因为它们都融入了人类的意识、计划和期望,刻上了人类意志的痕迹”。人类世界就是符号世界,“世界的本体就是符号”,从物符号到符号物,显示出人类主体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人类不但给予自然以意义,更不断创造符号本身,人类构造了他们眼中的世界。从媒介的角度,口语-身体媒介时代到文字-印刷媒介时代,可以大致对应社会符号构成从物符号到符号物的转变,而到了数字-网络媒介时代,作者提出人类进入了元符号的时代。但元符号时代意味着什么?人类不依然在构造他们眼中的世界吗?人类的确依旧,但人类构造意义的方式却越来越在各种问题中显现出客体的影响与模塑,人与世界的关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作者想借信息社会符号学观照的,除了对信息社会这一还在进行中的客体的理解,还有人的境遇问题。无论是过度连接导致的过度文化、后台翻转导致的伦理困境、装框导致的意义生态危机、数字鸿沟、还是超级人工智能到来后人类的终结,都显示出作者对人这一主体的忧虑与关怀。全书其实隐含着一条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线索:人有可能被其创造的东西所控制,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危机。在本书末尾的符号学批判部分,作者探讨了物在意义世界中的位置、身体与意义的关系的问题,指出必须确立物和身体在这个符号满溢的世界中的地位。笔者认为这可以算是作者从符号学出发为信息社会“寻找主体”的尝试,这也是作者一直在做的,当符号作为世界的本体,当使用符号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对“及物”和“具身”的呼喊把人类拉回到了人类最初使用符号和寻求意义的时刻、拉回到了人类主体刚形成的时刻,但无论是否存在那一时刻,我们终究无法回到过去了。其实意义本就是主客体的契合,完全自由的主体也可能只是一种幻想,但我们依然可以借此意识到我们正在缺失掉的部分,并在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中去建构我们的“美好生活”。寻找或重建某种主体,亦是寻找或重建某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