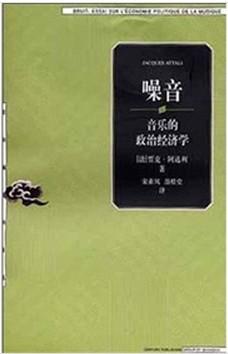
叔本华在《论噪音》一文中这样写到:“有杰出才智的人对任何形式的扰乱深恶痛绝,因为扰乱转移了或分散了他们的思路,尤其是噪音”。我们通常所说的噪音,物理学定义为“发音体不规则的振动产生的声音”,无非就是工地、马路、机场等处那些难以忍受的声音。而在符号学里,噪音可以有另外的定义。
叔本华在《论噪音》一文中这样写到:“有杰出才智的人对任何形式的扰乱深恶痛绝,因为扰乱转移了或分散了他们的思路,尤其是噪音”。我们通常所说的噪音,物理学定义为“发音体不规则的振动产生的声音”,无非就是工地、马路、机场等处那些难以忍受的声音。而在符号学里,噪音可以有另外的定义。《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区分出了两种噪音:其中一种便是指在符号接受与解释过程中,解释者认为对他的解释不起作用的部分。而贾克·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就对物理学意义的噪音进行了符号学的探讨:噪音干扰听觉,然而噪音本身并不存在,“只有当它和将它镌刻在其中的系统发生关联时方始存在:发射者,传递者,接受者”,人们对噪音的感受是一种对构建符码信息的侵袭,而音乐的历史就是噪音被接纳的历史。
阿达利首先指出西方知识界观察世界的一个错误:世界不是给眼睛看的,而是给耳朵倾听的。倾听音乐使得权力的运作得以实现,权力控制了音乐的生成,使一部分声音沉默。在这个音乐的秩序中,被压抑的噪音始终在反抗,这种反抗形成了阿达利所谓的“音乐政治经济学”:噪音即是对差异的质疑;音乐(秩序)则是对差异的继承。音乐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是我们能够从音乐的内容形式与传播接受中察觉出意识形态,而是音乐(准确地说是噪音)预言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
音乐预言论,这可以视为阿达利在这本书中最独特的见解。它不同于那些四处寻找偏方的知识考古(比如对排泄物的兴趣),阿达利不仅关注权力与话语,他希望“找出人类历史与经济变迁,以及噪音系统化为符号的历史之间的关联;用后者预测前者的演进;结合经济学与美学;阐述音乐是先知性的,而社会体制则与之应和”。为此,他把音乐文化史划分成四个阶段:牺牲(sacrifier)、再现(représenter)、重复(répéter)、作曲(composer),音乐就在这四个阶段中获得各自不同的合法性。
在第一阶段,音乐的功能是“一种牺牲的符码”。在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前,音乐还不具备完善的商业化条件,它还留存着最原始的气质,即一种从巫术、神话、宗教中得到的气质。阿达利认为,噪音是暴力,是扼杀,因为它通杀戮一样阻断了信息的传递,“是杀戮的拟像”;而音乐“是噪音的一种引导”,也是一种杀戮的拟像。于是在“牺牲”阶段,音乐体现出了一种杀戮仪式化的特点:“音乐在声音的领域中反弹,一如对牺牲导引暴力的回声:消除不和谐音以避免噪音散播”。这一时期,音乐成为统治者巩固权力的工具。朝廷教会利用音乐来进行朝拜的仪式,让人民在音乐中获得牺牲的崇高感,从而景仰统治者。
第二阶段,音乐成为了再现的符码。它将对杀戮的拟像变成了对杀戮的隐喻,并且尽量呈现出和谐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从14世纪开始,音乐的形式就逐渐从圣咏、赞颂发展为室内乐、奏鸣曲;音乐开始进入消费领域,并且由虔诚变为了享受和娱乐。音乐的消费化使音乐家摆脱了统治者的控制,并且使音乐家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完美的寂静。古典音乐会之中绝不容许有吵闹声,这种寂静是对音乐的臣服,是对那种人为的和谐景观的认可,由此这种寂静产生了音乐。阿达利认为再现的概念在逻辑上意含着交换和和谐,而这18世纪的音乐厅正预示了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20世纪的政治。他举例说“巴赫几乎探索了调性音乐系统里蕴含的所有可能性,甚至超过。他的作为显示了未来两个世纪中的工业拓展史”。
第三阶段,音乐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出现了重复。在这一阶段,音乐由集体的消费变为了个人的消费,于是再现时的“完美寂静”的要求被瓦解了。唱片业问世后,音乐与金钱的关系由当初的暧昧不明变得赤裸裸和夸耀起来,生产唱片成为了第一个生产符号的系统。在唱片时代,音乐所预示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如同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为了要累积利润,有必要出售可以储存的符号生产,而不仅只是它的景观”;“随着交易的成长,被易物品初始的用途也几乎消失殆尽”。这种符号社会更体现在,我们在参加演唱会或者音乐会时,获得的不是在现的体验,而是对唱片(符号)的拟像。在这个时代,音乐成为背景噪音,所有场所无时无刻不在播放着音乐。音乐的重复指明了重复性消费的存在,而这种大量的重复也阻隔了商品差异性的沟通。清一色的西方时尚塑身标准,就是最为明显的集体无差异方向。
第四阶段,音乐表现出一种允许人逃离仪式控制,再现错觉,重复沉寂的生产的终极形式——作曲。当代音乐越来越行为化,从对音乐会的反叛到对音乐创作的反叛,从鲁梭罗到凯奇,音乐在以行为为基础进化的时候,艺术家越发拒绝被金钱标准化——沉寂,这便是一种新的作曲的开始。这种作曲完全是为了作曲而作曲,并且不同于华彩即兴,是没有先文本的创作。“发明新的符码,在创造语言的时候也同时创造信息。纯粹为了一己的享乐,只有这样才可以创造新的沟通条件”。这种作曲式的政治事实还尚未发生,我们现在仍处于重复阶段音乐所预示的政治经济情形,但是阿达利认为作曲预示的是囤积在商品中的时间呗取代,作曲解放了时间。
阿达利的见解充满了洞察力,其著作出版后虽然被音乐界的学者斥为“噪音”,但是却受到了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和比较激进的音乐文化研究者的认可。有学者指出这本著述中缺乏对音乐作品的分析,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部宏观并且跨学科的著作而言,细致的音乐学作品分析意义不大,也不能增加论述的力度。阿达利充满创见地探讨了音乐与噪音,以及音乐发展史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关系,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拓宽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