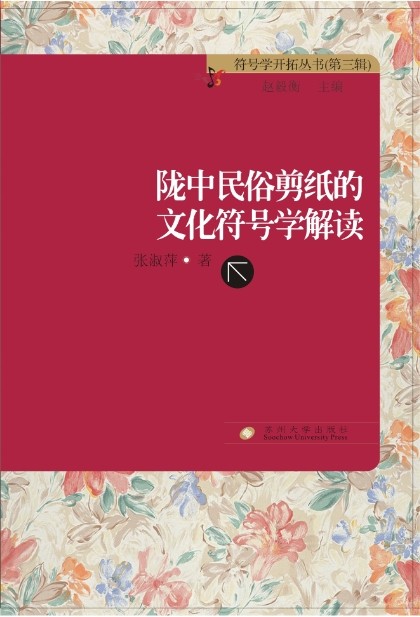作者:
朱林 来源:
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4152 2014-05-02 00:19:20
民俗符号学的广阔世界
——读张淑萍《陇中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民俗文化的象征体系,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及其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是形成民俗文化传承的要素。民俗符号学在学界早已有人倡导,但大多数并没有系统学习过符号学,所以大多数先行者也主要停留在套用语言符号学常说常道的“能指/所指”,“编码/解码”的阶段,结果“能指/所指”就被通俗地解释为“形式/内容”,而“编码/解码”也变得像做数学题一样。与此类似的现象是,很多学术专著和论文可以满纸都是“符号”,但可以没有一个“符号”是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满纸都是“叙述”,但可以没有一个“叙述”是叙述学意义上的“叙述”。但张淑萍女士的这本《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可以说是用理论符号学的系统知识解析民俗现象的佳作,已初具民俗符号学的这一宏大领域的模型。笔者初学尚浅,试从以下几方面赏析该书:
一,陇中剪纸艺术的元语言背景
“元语言”(metalanguage)本是语言学术语,语言学将语言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元语言就是谈论、解释对象语言的语言。在符号学领域,元语言本该叫做“元符号”,但起家于语言学的符号学借用语言学的术语已经约定成俗,无可厚非。元语言是符码的集合,而符码是对符号单元的解释,赵毅衡先生认为元语言的集合构成意识形态,所以这就自然构成了“符码—元语言—意识形态”的三层谱系。在张淑萍女士《陇中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梳理了剪纸艺术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这些是我们“正解”剪纸艺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该书第三章,作者从列维·布留尔有关原始隐喻思维入手,分析了剪纸艺术的图腾信仰、巫术、宗教背景。作者认为剪纸的原初文化功能应该是巫术灵物,而且越往前追溯,这种功能越强大。
二,民俗剪纸的系统分类
符号的任意武断性和像似性是关于符号特征常论不休的话题,皮尔斯与索绪尔很大的不同就是他认为符号具有像似性,根据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皮尔斯将符号分为三类,即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convention)。像似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仅仅借助自己的特征去指示对象,不论这样的对象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它都拥有这种相同的特征。换句话说,符号可以再造对象,例如作者在该书中说到的龙,凤凰,麒麟等形象,虽然符号看起来很生动很形象,但其模仿的对象是虚构的不存在之物。更进一步,作者根据皮尔斯关于像似符号更细致的分类,描述了剪纸艺术中的形象像似、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指示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通过被某个对象所影响而指示那个对象。就指示符号被对象影响而言,它必然与那个对象共同具有某种质,就此而言,它指示那个对象。指示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大多表现为时间上的接续关系或者空间上的邻接关系。在分析民俗剪纸的时候,作者很诗意地说:“剪纸纹样中出现的一朵花,一只蝴蝶,一棵树,其意味绝不仅限于此花,此蝴蝶,此树,而是指代百花盛开,蝴蝶翩翩,林木葱翠。从而隐喻春意盎然的春天景象,也以自然界的美好类比人的生活和情绪的舒畅,让指示符号与像似符号之间产生跨界”。规约符号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借助法则和常常是普遍观念的联系想去指示对象。作者说明了剪纸中剪纸的色彩、主题、适用场合等为何呈现如此如此的规约。针对剪纸的符用对象,作者将剪纸分为事人剪纸、祭祀剪纸和巫术剪纸。整体来看,事人剪纸在体现剪纸作为物而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表达着实用意义,也释放出艺术意义。祭祀类剪纸主要用于祭神和祭祖,其中祭祖剪纸占了十之八九。巫术剪纸作为与祭祀剪纸、事人剪纸相对等的一类民俗剪纸,至少有两类,即刻效验性和预防诱导性。前一类用在难产、重病、叫魂等实用场合;后一类兼有巫术和装饰功能,主题多样化,主要包括辟邪、镇宅、祈福等。洛特曼在《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一文中将文化分为主要指向表达层面的文化和主要指向内容层面的文化,主要指向表达层面的文化,如严格仪式化的行为,强调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一一对应的关系,二者不能分开;主要指向内容层面的文化,其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的联系相对自由,如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剪纸符号在实用意义(事人、祭祀、巫术等)艺术意义的滑动,也就是说洛特曼两种文化分类之间的摆动。
三,剪纸的符号修辞分析
赵毅衡先生在其《符号学》一书中说比喻往往被认为是语言的最本质特征,整个语言都是比喻累积而成。任何符号体系也一样,是符号比喻累积而成。在张淑萍女士《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这本书里,作者详细分析了其中隐喻、明喻、曲喻、转喻等符号修辞。在陇中民俗剪纸中,这隐喻普遍存在。比如花瓶和葫芦,因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肚大,与怀孕的母体之间存在客观上的相似性,于是这两个不相关的事物间被人类赋予关联,将花瓶、葫芦(喻体)投射到母体子宫(本体)上,形成互动,使之成为生育的符号。在分析提喻时,作者认为在剪纸符号中,提喻的本体与喻体间的关系有单数与复数、类与属、部分与整体三类。象征是符号符用理据性的累计,在文化传统中,剪纸艺术对于族群感和认同感功莫大焉。
四,剪纸艺术的双轴操作
索绪尔将语言的双轴操作分为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聚合)。雅各布森在此基础上更明确提出了选择轴和结合轴。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一书中说“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形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组合就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可以说,聚合是组合的背景,组合是聚合的投影”。张淑萍女士在书中介绍了“阴剪”与“阳剪”两种剪纸手法,这一特征与雕刻印章同理。但笔者认为这种手法用于分析“背景/前景”似乎更恰当,对于分析符号双轴关系似乎并不明显。组合与聚合的二分意义不止如此,可以说某些文化的组合特征更突出,某些文化的聚合特征更突出。
洛特曼在《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一文中说,对立和替换是人类创造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中两种主要的区别原则。其实在这些符号学机制中就蕴含了人类学所说的“集体性选择”与“集体性失忆”,被记录下来的部分成为无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中的“幸运者”和“幸存者”。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文化都是选择与结合,或者说组合与聚合双轴操作的结果,剪纸艺术是滚滚洪流的历史中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