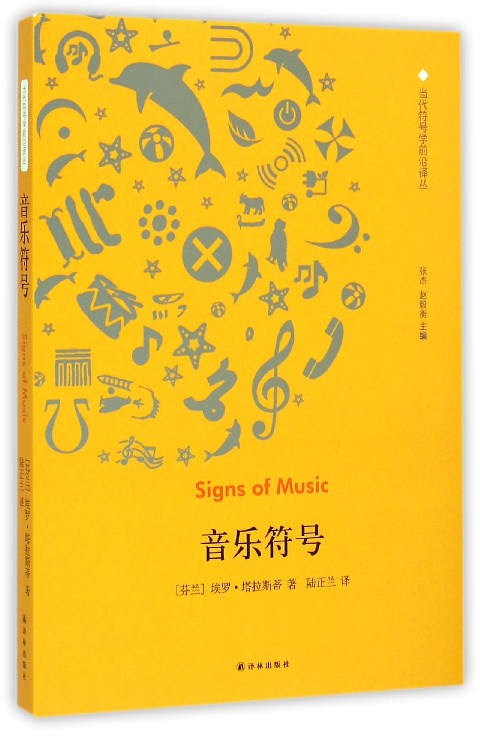
音乐是符号,音乐界无人怀疑。音乐符号如何表意?却很少有人说清。音乐符号学,在中国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已有介绍,但因为种种原因,理论介绍和研究都没有长足推进。这不是音乐界学者的能力问题,而是音乐意义的特征造成的困惑。然而符号学这个工具如此有用,音乐学的研究者总得熟知。陆正兰教授翻译的这本中译本《音乐符号》,论述通俗简明,音乐分析生动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符号学研究的门径。
解开音乐符号学的难题——评塔拉斯蒂《音乐符号》
(芬兰)埃罗·塔拉斯蒂,《音乐符号》,陆正兰译
译林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刘小波
音乐是符号,音乐界无人怀疑。音乐符号如何表意?却很少有人说清。音乐符号学,在中国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已有介绍,但因为种种原因,理论介绍和研究都没有长足推进。这不是音乐界学者的能力问题,而是音乐意义的特征造成的困惑。然而符号学这个工具如此有用,音乐学的研究者总得熟知。陆正兰教授翻译的这本中译本《音乐符号》,论述通俗简明,音乐分析生动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符号学研究的门径。
本书作者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音乐学教授,钢琴家,世界符号学会前会长,欧洲科学院院士。多年来一直从事音乐符号学研究,著作等身。在符号学界,塔拉斯蒂的研究继往开来。
符号学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以皮尔斯、索绪尔等人为代表,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理论基础是逻辑学和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符号学在六十年代兴起。塔拉斯蒂的理论源泉看起来十分驳杂,但依然能有一个清晰的路向。他年轻时师从格雷马斯,可谓格雷马斯的“巴黎学派”的忠实弟子。但他对第二代符号学“只是把经典符号学放到了知识论的背景之下”不满,试图将存在主义哲学和符号学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存在符号学,因此它的立场是对第二代符号学的发扬与修正。选择符号学作为途径,就是因为符号学是意义之学。格雷马斯说的很明白,“要知道,符号学形式其实并不是别的,它就是意义的意义。”[1]
塔拉斯蒂的哲学理论,都与音乐这一最为抽象最具哲学意味的艺术形式联系起来。“能量场”、“强/弱符号”、“阐释者/被阐释者”、“此在-存在”等观点都与音乐相关。他的音乐符号哲学之旅还涉及一系列概念,例如“内在的范畴和外在的范畴、理解与误解、焦虑符号、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符号与价值、后殖民符号、景观符号、场所符号、广告符号、迪尼斯符号等。”[2]音乐家出身的塔拉斯蒂用符号学的理论介入社会,用音乐这一媒介探索社会和人生的哲理。音乐、符号、社会、存在四位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塔拉斯蒂音乐哲学理论体系。
格雷马斯曲高和寡的理论,在他的学生手中不断被修正。塔拉斯蒂就是其中之一,他将其它理论并受兼容,一大串的名字与之相关:索绪尔、皮尔斯、雅克布森、洛特曼、巴尔特……伞形批评理论的一支——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在他那里真正融合。通过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有效地推进理论的进程,在他看来,“音乐符号通过两方面变得活跃起来,一是实践,即聆听和演奏音乐,另一方面是对历史、美学的体验”(此书序言)。很明显,塔拉斯蒂两方面都兼顾到了,并且还建构出一种理论,一种话语。正是这种话语,不断推进着音乐研究的进程。
《音乐符号》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体论述音乐作为符号,具有纲领性质。分别论述了音乐何以是一种符号、史学视域中的音乐符号以及音乐情境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性别、生物学和超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音乐中的身体与姿势。第三部分是社会和音乐实践,从社会视角介入音乐,探讨与音乐相关的声音、性别、身份、民族、教育等多个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塔拉斯蒂首先肯定了音乐是一种符号交流。其理论源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塔拉斯蒂认为“语言中所有的一切都有远初的意义,而我们聆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也不可抵挡地渴望用感受向音乐灌输意义”。接下来塔拉斯蒂讨论音乐的意义表现方式问题,指出音乐不仅是多种符号文本中的一种,音乐也是一种叙述。
作者还介绍了两种符号学研究的范式及其对音乐研究的适用性。皮尔斯模式重点在于解释项概念的引入,使得音乐符号学成为一种意义之学;格雷马斯模式的渊源则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最后,作者将对音乐的理解提升至对存在的理解,他的一以贯之的观点是:“通过音乐我们超越存在的情境。”
所谓音乐情境,作者指行为和事件这一对核心概念。当艺术体验这样的奇迹出现在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中时,艺术会从一种行为转变成一个事件。因此,每一曲音乐的背后,存在一个‘隐含作曲家’,这个人格是“解释社群的读者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一套意义价值。不同的文本,不同边界的文本,有不同的隐含作者。”音乐乐曲的文本与伴随文本,都指向音乐的情境,正是这些音乐情境而非单纯的乐谱与演奏构成了音乐。
我们解读音乐,其实就是借助音乐情境寻求背后的隐含作曲家,建构类似的“拟主体”,从而寻找文本的意义—价值观,这样才能解读音乐作品。无论塔拉斯蒂怎样强调音乐自身的结构与形式,他最后都会回到价值这一点上来。也即是说,音乐的最终意义是由接受者解释出来的。
全书的第二部分分别讨论音乐中的性别、生物学和超越,身体与姿势,尤其仔细地分析西贝柳斯作品的有机性,分析肖邦音乐中的身体性与超越性。这是全书分析最独到的章节,也典型地显示出音乐符号学被誉为解放了的新音乐学的分析范例。
此书最突出的地方,是讨论音乐的社会实践。从本质上讲,音乐是属于社会的,社会学的介入使得音乐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音乐是社会的产物,尤其是音乐中的身体性,在分析肖邦作品时,作者以肖邦的《F小调幻想曲》为例,列举出作品中35种不同的身体言说,这36种言说方式中,身体特征都会出现,有时明显,有时隐晦,但每一种方式中都会陷入社会化、文明化与自由个性化的冲突。此外,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一系列问题:音乐的超越性、民族性、歌唱者的社会身份、音乐教育、歌唱的意识形态等,这样具体化后,音乐的社会符号学研究就落到了实处。
即兴表演和表演艺术是音乐学的重要议题。在这里,塔拉斯蒂发展了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升格为Z型方阵。通过这样曲折的辩证关系,“表演就成了演员自身从本色自我,升向本色的非我,从‘总的个人事实’向‘总的社会事实’的一步步过度。音乐符号表意过程,就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生成过程。如此的表演艺术符号过程,使音乐脱离了与生物性本能模仿,脱离了表演的纯身体性,而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3]通过这样的建议,强化了音乐的表演特质以及演示类艺术体裁的归属。从叙述分类来看,音乐属于演示类叙述。演示类叙述,即用身体、实物作为符号媒介的叙述。其特点为“展示”、“即兴”、“观者参与”、“非特制媒介”等。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演示类叙述可能是与人性最相契的叙述方式。而且,随着当代文化越来越重视身体的符号表意,演示叙述正迫使我们给予学理的重视。[4]
欧洲音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前学科时期、阿德勒体系时期和后阿德勒体系时期。前学科时期关注音乐的“形式”和“功用”,但是缺乏“历史”的视野;阿德勒体系补充了“历史”的视野,又失落了“文化”的视野。而后阿德勒体系时期则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形成了历史、体系和文化的三大研究领域。[5]音乐研究又有“旧音乐学”和“新音乐学”之分,旧音乐学聚焦音乐文本本身,而新音乐学跳出文本,关注音乐与性别、话语、身份、表演、地域、观众等更广阔问题的关系。
毫无疑问塔拉斯蒂的音乐符号学,属于西方音乐研究的阿德勒体系,关注音乐形式、历史的基础上,挖掘音乐的文化内涵;他也是属于“新音乐学”派的,音乐符号学,是新音乐学运动的核心方法。塔拉斯蒂的研究也明显代表了新音乐学的研究模式。
塔拉斯蒂本人认为本书的目的是提示音乐研究实践的路子:“是为音乐符号学提供一本或多或少的‘实用指南’”。也就是说,本书是对音乐作为符号和交流的研究”(该书序言)。除了应用研究,本书还是基础研究,许多观点具有纲领性。正如译者后记所说“ 这本著作更像是一个宽厚的基地,为我们拓展了关于音乐符号的想象,以及在此之上建构文化意义的多种可能性。在此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套具有说服力的音乐‘元语言’:音乐是一种情境,音乐具有身体性,音乐是个人、社会、文化的互文本,音乐聚集了声音、性别、身份、民族、教育等多重因素。”[6]
符号学为音乐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范式,一旦掌握这一套方法,就会看到别样的风景。符号学的介入使得音乐研究变成一种阐释解读、一种再创造的过程。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音乐必然有意义,因此音乐必须是一种符号。只是音乐符号的意义很难用语言说清楚。当音乐印成乐谱时,它是一种记录式的符号;当它被演绎成声音时,它又成为一种声音符号。应当说,没有音乐符号学,我们已经无法对付音乐学研究提出的大量问题了。符号学为音乐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提供研究思路、研究视阈和研究范式。
意义有三种:意图意义、文本意义、接受意义,音乐的意义并不例外。意图意义是作者要表达的意义,接受意义是读者获得的意义。而“内在意义是符号学家、内容分析家和形式内容的学者们试图发掘的意义”。[7]音乐符号学探寻的是这三种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乐曲文本内在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音乐作品本身的结构式分析。音乐十分神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自律性最强的艺术,也是最少表意的艺术。符号学的引入,能解读出更多的意义。正因为这个理解,符号学研究本身扩大了音乐学的领域。
符号学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影响到存在世界的方方面面,音乐的意义虽然比较隐晦,却也不例外。符号学给音乐研究提供了一套元语言、一种新的视角。塔拉斯蒂对音乐意义追寻,给我们的音乐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启示。
作者:刘小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
联系方式: 13730812317
邮箱: 576025628@qq.com
邮寄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当代文坛编辑部 610012
[1](法)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吴泓缈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2] 魏全凤,《存在与符号——塔拉斯蒂的存在符号学简述》,《符号与传媒》,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陆正兰,《表演符号学的思路——回应塔拉斯蒂的<“表演符号学”:一种建议>》,《符号与传媒》,第5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5] 李方元,《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及其三个历史阶段——特征与文化阐释》,《音乐研究》2015年第1期。
[6](芬兰)埃罗·塔拉斯蒂,《音乐符号》,陆正兰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译者后记。
[7](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探索美的艺术及流行艺术》,章浩、沈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