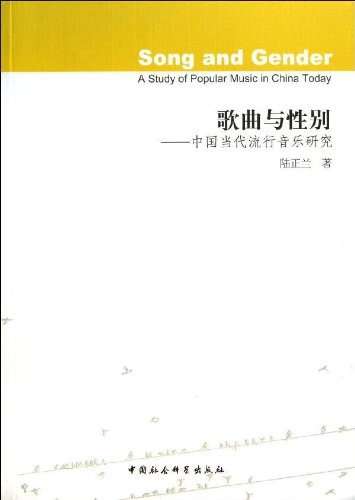
《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以歌曲与性别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著从研究方法和立场来看,采用了内外兼顾、点面结合的符号学研究 ;在详实的例证基础上,既深入阐释了流行音乐保守的性别表意特征,又敏锐地看到其所蕴含的性别变动新态势,这不仅是对中国当代流行文化研究困境的突破,也成功地实现了符号学研究的“落地”,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文化符号学研究力作。
中国性别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突围
——评陆正兰《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
王小英
摘 要 :陆正兰新著《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以歌曲与性别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著从研究方法和立场来看,采用了内外兼顾、点面结合的符号学研究 ;在详实的例证基础上,既深入阐释了流行音乐保守的性别表意特征,又敏锐地看到其所蕴含的性别变动新态势,这不仅是对中国当代流行文化研究困境的突破,也成功地实现了符号学研究的“落地”,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文化符号学研究力作。
关键词 :《歌曲与性别》;符号学 ;中国文化 ;流行音乐
当代语言符号学专家王铭玉先生曾先后于2013年 第四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及2014年四川大学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开题会上指出,语言学要上天,符号学要落地。诚然,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却指出了存在于符号学界较具普遍性的情况,即符号学学术框架与社会现实脱离。按理说,符号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公分母,符号学理应成为分析解释各种文化现象的有效工具,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符号学悬置在天空,难逃“空洞理论”的责难。 赵毅衡先生始终坚持认为符号学即意义学,而文化就是人类所有表意活动的集合。如此说来,符号学理应成为研究文化这种人类表意活动的最佳方法,才能不负其“人文学科公分母”的美誉。在国外,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法国人文 科学话语的符号学分析已经颇有成效 ;但在中国,除了用中国的例子为国外学者的理论观点做注脚,拾人牙慧之外,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较为成熟的符号学研究依然是凤毛麟角,具有说服力的研究例证更少, 以至于“公分母”这一说法,难免有国内符号学者们 借吹嘘研究对象而自我拔高之嫌。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符号学研究背景之下,陆正兰教授推出的《歌曲与性 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以下简称《歌曲与性别》),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圆融的学术推理,有效改变了这种“符号学落地”的研究局面。
目前,符号学的应用大致有两个方向 :一是将其它各种理论学科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理解,也即门类符号学,如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广告符号学、游戏符号学、符号叙述学等 ;二是用符号学来解释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具体符号现象,也即狭义上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实践。前者近年来已有颇多进展,但在后者上,虽然间或有一些成果,但普遍较为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而陆正兰的《歌曲与性别》可谓中肯深入。
《歌曲与性别》是陆正兰继2007年的《歌词学》之后的又一本力作,也可视为《歌词学》的姊妹篇。 从作者的学术历程来看,《歌词学》一书就已是作者学术生涯上的一里程碑事件,它一方面标志着作者研 究境界的提升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者找到了 一个值得深挖的学术富矿——音乐文化学。但《歌词学》主要的关注点还在于歌曲中的“歌词”,借用李诠林的话来说即“是一部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歌词研究专著”1,对当代流行歌曲的关注并不是太多。此后的7年间,作者的学术视界进一步扩大,关注对象也从歌词学扩展到整个音乐文化领域,期间发表了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涉及音乐伦理、歌曲 性别、传统音乐文化、音乐符号表意等诸多议题,并 翻译出版了《音乐•媒介•符号 :音乐符号学文集》(四 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这一国内第一部音乐符号学 译作,成果颇丰;而作者对歌曲持续的关注和不断的 探索,终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歌曲与性 别》的诞生。《歌曲与性别》无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 还是在思维的缜密性上,都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说,在《歌词学》中,作者在借用理论分析歌词现象时还稍有“理论先行”的嫌疑的话,那么在《歌 曲与性别》中就已完全摆脱了这一倾向,理论似为其 作品而生,使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理论本 身因“门类限制”2而产生的局限,也在流行歌曲研 究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弥补。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 面对陆著作一解读。
一、符号学研究路径 :沿着核心线索展开与点面结合
约翰•迪利在其《符号学基础》(第六版)中指出, “符号学观点是一种视角,它产生于持续地思考一种 简单的认识,并追踪其后果 :从最原始的感觉的根源直到完成细化的理解力,我们的全部经验是一张用符号关系构成的网络或织网。”符号学视角首先与经验有关,它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诠释框架,可以摆脱观 念论和实在论的局限,建立对“现实”的全新理解“:它发生在与‘主体的’存在和每一个‘主体性’相对立 的‘客观的’概念中。”也即,所谓现实即是符号 构筑的,介于主体的存在和概念构筑的“客观性”之 中的。《歌曲与性别》中对流行音乐的关注便贯穿着 这一立场。因此,虽然歌曲与性别是核心线索,整个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是符号学的。《歌曲与性别》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有两个着眼点 :歌曲和性别。流行歌曲是流行音乐之重要构成部分, 因其有表意清晰之歌词与优美旋律的配合,故也是对 大众影响最大的部分。性别是人类文化之重要向度,
《老子》曰 :“无名,天地始 ;有名,万物母。”(第一章) 所谓“始”《,说文•女部》云 :“女之初也。从女台声。” 女之初,即女子初潮,女子生理性别特征初现时,男 女才出现生理差异,后“始”字演绎出“分别”,即“无名” 乃是天地混沌初分之时 ;所谓“母”《,说文•女部》曰 :
“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由此母当 训作化生养育,此即有名之时,乃是人类化育出来之后的事情。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文化从女性之化育生养命名万物开始。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先从女 性之社会性别分工开始,社会性别的分界是人类文化之重要的、原初的区分。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人类其它丰富多彩的文化。因此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抓住了歌曲和性别,也即掌握了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歌曲与性别》结构上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关注 的重点是歌曲文本,外篇的关注点是歌曲文化中的传 播机制及趋势,二者都由性别这一主线贯穿始终。内外两篇的划分参照了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 和外部研究的做法,既照顾到歌曲文本本身的巧妙细 微之处,又将其放之于社会文化世界中去理解,避免 了文化现象研究中常见的两种误区 :第一种是陷入纷乱复杂的文化细节中不能自拔,缺乏必要的理论提升 ; 第二种是将文化现象过度抽象为概念理论,凌空虚蹈, 成为空中楼阁。第一种虽然扎实,然未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显得小家子气,第二种虽然貌似深刻,但未 免有卖弄术语故作高深的嫌疑。因此,能将二者的关 系处理好也就成了文化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化现象研究 的一个难点,然而这一当代文化研究的难题在陆著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陆著内篇部分大致上又可以分成两大块,第一章和第二章谈歌曲结构以及(歌词)表意模式中的性别问题,第三章到第六章是对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划分及分类解析。外篇部分先从符号过程和伴随文本的角度来谈歌曲的文化性别,再去解读歌曲中的叙述伦理转向,女性歌曲、摇滚歌曲和“中国风”流行歌曲, 将之与当代社会大语境相关联,从其符号的角度作出文化判断。
当下流行歌曲杂乱多样且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以 研究者有限的个体之力如何能把握,且做到不失公 允,这是首先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陆著的处理方法是选样,以“百度MP3”为主,综合“QQ音乐”“中 国歌曲流行榜”等,这的确是一种比较巧妙的取样方 式,虽然不能完全客观地展示流行歌曲的全貌,但考 虑到中国社会的网络普及率及网络化进程速度的进一步加快,的确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歌曲的“流行”程 度。当然作者也未忽略“排行榜自身催生排行榜”的性质,在“反弹单轴化”时代,这几乎是当代文 化现象中的一普遍特点,马太效应产生之重要缘由。
内外两篇的结构安排和研究对象的选取方式说 明,就已经奠定了《歌曲与性别》的逻辑深入路径, 即从歌曲文本到歌曲文化,从文本细读到文化观照, 从文本性别到性别文化,层层交织却又问题意识明确 : 围绕着性别来谈流行歌曲,围绕着流行音乐来进行性别研究。这样很好地解决了文化细节与理论推演之间 的关系,破解了文化研究中的难题。
二、文本的性别表意 :呼应结构中的性别与 文本性别身份
“呼应结构”是“歌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体制不变 的原型基础”,也是陆正兰歌曲研究的独创。早在 其《歌词学》中,她就明确发现并提出,呼应结构是 基于歌曲传唱目的而产生的“歌词最本质的结构特征”,在歌词内部、歌词与音乐、歌词与文化之间 都存在着呼应。但这层层的呼应中,社会性别如何表意,却是个复杂但值得探索的问题。陆著以其特有的 方式细腻而深入地剖析了其中的性别赋形。
中国流行歌曲歌词中的自然成对,是歌词内部语义上投射出的性别概念隐喻,它与人类的性别文化结 构相关。并且,歌词与音乐的性别呼应,虽然有其基 于男女生理性别的考虑差异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人 为的非理据性的一面。作者对当代流行歌曲表意模式 的分析及阐释,展现了符号文本表意的曲折复杂过程, 它不仅关涉到文化的规定性,并且还在这种规定性中,通过言说主体的或隐或显,或个体或群体的方式传达出不同的性别意义 :性别交流最为直接自然的方式为 “我”“你”同时出现 ;性别关系的曲折表达,经常通 过隐藏“我”“你”中一个的方式来达到;当代人情 感的复杂性,在第三人称或多人称组合变体中更能反 映 ;性别建构中影响最小的为“我们”和无人称关系 歌曲9。这就将不同的形式之于性别建构之价值,区分出了等级。此可谓陆著的一大研究贡献。 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任何文本都有身份,也即普遍文本身份,“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无法表意。 不同的文本身份,要求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释。”个人的身份具有不同的面向,如社会身份,性别身份, 民族身份等等,文本也应有多重身份,但歌曲文本的 性别身份,是否如同人的社会性别身份那样清晰明 确?它的性别身份由哪些因素来决定?《歌曲与性别》 以大量文本实例为基础,指出在歌曲生产和流传的多 重主体的性别建构中,虽然也呈现出文本的性别身份, 但“歌词的文本身份,也体现了歌曲文本的性别身份”。“在歌词中,歌曲的‘我对你说’的基本表意模 式,以及歌词中的文本性别标记,会给各种的言说者 和言说对象以性别规定。”歌词的确是歌曲构成中 最明确的部分,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其性别身份的 参考点。因此这一标准也确是最有效和简练的。需要指出的是,陆正兰并没有将歌曲的性别身份分类,简单地与人类性别的二分法对应,而是从文本实际考察出发,很智慧地将其分为五种 :男歌、女歌、男女间歌、跨性别歌及无性别歌。男女间歌指的是对唱的歌 曲,跨性别歌指的是歌唱实践中男女可以互换传唱的歌曲,无性别歌是没有明显的性别色彩的歌曲。这种 分类方式比较复杂,但比之于将人的性别身份简单地 划分为男女的方式却要精确地多,也更为贴合流行歌 曲的实际情况。男歌和女歌都属于性别色彩浓烈的歌 曲,比较容易辨别。难得的是后三者的区分,如果划分标准不能将对象基本隔开,也就意味着标准的失败。 男女间歌和跨性别歌的区别在于对唱和换唱的区别, 共同之处在于都形成一种性别对话关系。无性别歌的 特点在于性别意识的隐藏和由男女共同构成的“我们 性”的彰显。如此一来,多样的歌曲文本就呈现出大 致清晰的面貌,也为进一步的特征考察提供了基础。
从女性研究发展到性别研究,男性气概也被考虑 在内,人的性别身份其实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而这种 复杂性又常常落实在各种性别表意的实践中,作为人 类符号活动之一种的歌曲之性别身份,从未被如此详 细而缜密地考察过。所以,一旦基于这种情形进行考 察,结果也发人深思,男歌与女歌在选材上、迷人点 上和意象使用上的差异表明 :“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 在形态上已经极端不同,但在其流行层面上,对意义 的解释符码实际上相当一致。也就是说,在基础的道德意识上,在性别的区分意识上,在性别道德上,与《诗经》中三四千年前的祖宗相比,我们至今行之不 远。”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保守一面的解 析相当的一致:“文化工业所夸耀的进步以及不停地 向我们提供的所谓新东西,不过是千篇一律之物的不 同伪装”。披着当代外衣的男女流行歌曲,其内核 竟然是一颗苍老的文化之心。并且,无性别歌看似没有性别意识,实际上隐藏着社会性别文化意识形态,借用语言学中首先提出的、并由赵毅衡发展了的文化 “ 标 出 性 ”( 异 项 ) 概 念 , 作 者 观 察 到 :“ 无 性 别 歌 表 达的情感,形象标准,实际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以
男性标准置换全民标准,从而覆盖了女性的声音。” 这是从歌曲的角度证实了,人类性别文化中偏向男性的父权制文化现实。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流行歌曲只是在固化既有的 性别文化身份,因为在附录部分我们看到男女歌总共 只占到36%,比例最大的是跨性别歌(占44%)。“跨 性别歌曲文本是展示一个人身上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 两种属性,以便提供两性沟通的一种方式。两个个体 不可能达到完全理解,但我们可以作无限的努力。” 这正是作者对流行歌曲性别新意的洞见和其性别平权 意识立场的期望。
三、文化的性别表意 :歌曲的传播机制与性别构筑趋向
流行歌曲是比较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大众文化 产品有一定的生产范式,经常是群体协作的结果,因此呈现出来的很少是单一主体的意识,流行歌曲亦不 例外。关于当代流行歌曲的符号过程,陆著指出其有 包含生产与传播的五个基本环节 :歌词——音乐—— 表演——媒介——传唱,这是最简符号过程“发送 者—符号信息——接收者”在流行歌曲这种文化实 践中的复杂展现。作者明确提出这五个环节中哪一个 环节都不具备充分主体性,存在的只是胡塞尔意义上 的共同主体性,“意义不是在主体自身中孤立形成的, 而是在主体之间的发送-接受过程中形成的”,歌曲 流行中呈现出各种意图意义、歌曲本身的文本意义和 接受者的意图意义循环融合的现象。因此,歌曲的性 别意图意义首先在曲调创作、歌词创作中呈现,并进 一步在歌词文本中确定好性别代言,然后再被具体的 歌手进行性别赋形,最后到达歌众那里,被具有能动 性的歌众予以性别表意的在场实现。符号意义生成的 复杂性在不同的文化实践中会带上各自不同的特征, 在当今信息媒介社会的大语境中,只要是流行的都无 法只是某个单一主体的主体性,小说、电视、电影、 游戏等都是如此。因此,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流行歌 曲,其符号过程中的性别赋形就是文化中的性别表意。
由歌曲文本到歌曲文化,伴随文本是连接二者的 重要桥梁。赵毅衡对伴随文本较为完整的归纳分类为作者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参考,歌曲的伴随文本, 也即其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和 先后文本中携带的性别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对歌曲性别的解释。《歌曲与性别》以CD封面这种 副文本为例,通过取样调查统计,发现男女歌手专辑 封面在身体表现程度上、色彩上、表演性和背景搭配 上以及和作品题目的关联度上,都有着明显的性别差 异。它们虽然以千差万别的“个性化”方式出现,但 却始终摆脱不了社会性别文化的投射,在相当的程度 上是“标准化”了的。CD封面这种伴随文本,参与 到对歌曲的消费中,它所建构的性别意义也成为争取 歌众认同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意义上而言,伴随文本 不仅参与歌众对歌曲文化意义的理解,影响到他们的 消费,同时也积极主动参与了歌众的主体建构。而伴 随文本的建构在相当程度上为的是流行,于是在制造 或添加这些伴随文本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与性别文 化同谋,同时也就使伴随文本在性别文化建构方面表 现出对既定性别文化很强的趋从性。而且,对歌曲的 接受本身也呈现出性别差异 :“女性更倾向于靠拢社 会文化规范,被动地接受歌曲传递的各种信息。” 女性比较执着地去模仿某个歌星演唱,本身就是一种 伴随文本执着,在这种执着中她们的主体身份也在一 定程度上被建构了。歌曲伴随文本在性别文化解释和 性别主体建构中的作用,被以具体而深刻的方式得到 了生动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歌曲千年如一日,实际 上,当代流行歌曲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向以抒情为主导成分的中国歌词,在当代流行 歌曲中其叙述成分愈加彰显,贯穿的是新的性别伦理。 虽然在女性歌曲中,女性仍然在“自我矮化”,但摇 滚歌曲的雄性特征在蜕化,90年代以后朝阴柔化方面 转向,21世纪初出现了以性别间歌为身份的摇滚歌曲, 尽管阴柔化不等同于女性化,但它意味着在传承社会 既有性别关系上,男性也不堪其性别角色之重,用阴 柔化的方式来自我疗伤。并且,与之相应的另一表现是,焦虑在男歌中比女歌中更为突出,怨男歌远超怨 女歌。雅各布森用“主导”说来阐释文学艺术的演变 时,指出演变虽然是核心成分和边缘成分的转换,但 转变具有共时特征 :“转换和变化不仅要根据历史上 的演变来陈述(首先有A,然后A1出现并代替了A), 而且那种转换也是一种直接经历的共时现象,一种相应的艺术价值。”女歌的自我矮化和男歌的阴柔化同时共存,正是社会性别秩序变化中的现象。
结语
仅仅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谈《歌曲与性别》,似乎 其只是符号学理论的一种比较好的脚注而已,这么一 来就矮化了此书形象。实际上,该书的逻辑性很强, 作者始终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现象为出发点,面对歌曲的种种特征,借用包括性别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心理学、社会学、谱系学等合适的理论方法,去深入 理解现象背后的文化规约、文化心理,文化操控规律 及文化走向,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也正因此它并没有 流为符号学的简单注脚,而是有着自己品格的歌曲性 别文化研究,也成为符号学应用的一个典范。例如, 作者在注意到男歌比女歌题材表现范围宽泛这一状况 时,就借用了两性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来加以解释,因 为男性具备的是“工具性心理特质”,女性具备的是“情感性心理特质”,男人的价值来自于自我定义,女 性的价值来自爱的关系,所以男性更看重事业成就、能力、报酬等,婚姻家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女性则 更看重爱情婚姻家庭。这一解释显得合情合理。再如, 对女歌编码中出现的主体自限,也即女性主体将自我 价值限制在被男性注视和欣赏上,这一异形编码的文 化控制方式进行理解时,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 说法予以阐释,性别意识形态通过一种结构而不通过“意识”,被从无意识的男性那里转移到无意识的女性 那里,由此女性自己主动陷入一种由男性性别控制的陷阱中。歌曲文化性别分析的批判立场也由此彰显。 而陆著也在这一系列的创新突破中彰显着其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