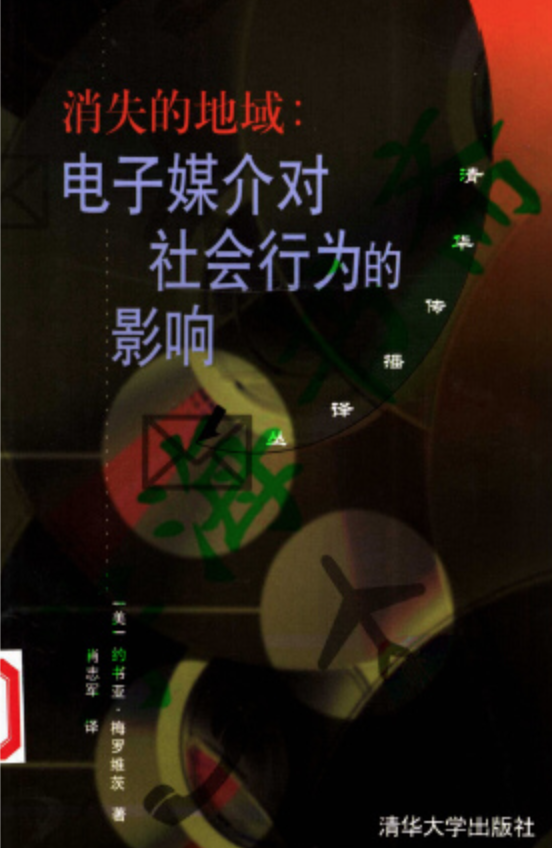
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欧文·戈夫曼将社会生活描述成多幕戏剧,我们身处其中,只是根据不同身份进行着相应的戏剧化表演。正如他自己所说:“说真的,这个世界也就是一场婚礼。”他的观点影响了许多人。这其中就包括本书的作者: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梅罗维茨的这本《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书中,他多次对戈夫曼的理论进行应用和引申,尤其是“前台”“后台”的观点贯穿本书始终。除了戈夫曼以外,麦克卢汉的观点也促进了梅罗维茨的思考。
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康亚飞
引言
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欧文·戈夫曼将社会生活描述成多幕戏剧,我们身处其中,只是根据不同身份进行着相应的戏剧化表演。正如他自己所说:“说真的,这个世界也就是一场婚礼。”
他的观点影响了许多人。这其中就包括本书的作者:约书亚·梅罗维茨。
在梅罗维茨的这本《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书中,他多次对戈夫曼的理论进行应用和引申,尤其是“前台”“后台”的观点贯穿本书始终。除了戈夫曼以外,麦克卢汉的观点也促进了梅罗维茨的思考。
麦克卢汉将传播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语传播、书写或印刷传播以及电子信息传播。而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家们恰好也对每一个时期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瓦尔特·翁对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中的不同意识模式进行了分析,伊丽莎白·艾森斯坦强调了书写到传播的意义,而梅罗维茨在本书中对印刷到电子媒介的研究正好是前者某种形式上的承接。
但在梅罗维茨看来,无论是戈夫曼还是麦克卢汉,他们的理论都不够完善:“戈夫曼显然忽略了角色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而“麦克卢汉虽然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角色的变化,但他没有清楚地解释电子媒介‘怎样’和‘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变化。”于是,他把二者的理论结合了起来,并尝试进行新的探索。
梅罗维茨的探索围绕着“媒介、场景和行为”展开,事实上,他在书中的所有论述也正是以这三个关键词的关系为脉络,然后从社会角色的角度切入,从而论证了“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的变化所带来的的潜在影响。
一、两对关系:新媒介和旧媒介的关系以及区域和场景的关系
1.新旧媒介的关系
关于新旧媒介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围绕该问题也引发了一连串思考:新媒介优于旧媒介吗?新媒介的出现是否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新媒介能否取代旧媒介,致使旧媒介的彻底消失?新旧媒介在社会进程中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大家莫衷一是。尼尔·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的发展以消解旧文明为代价,而这种旧文明在他看来是更加理性的文明,因此他对媒介发展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持批判态度。保罗·莱文森与他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媒介的进化过程,就是新媒介对旧媒介的“补救”过程,后一种媒介比前一种更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他也被人们归为“技术乐观主义”。在本书中,梅罗维茨开篇伊始就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书写并没有破坏口头论述,但是它改变了演讲和个人记忆的职能。类似地,电视并没有淘汰阅读和写作,电话也没有淘汰写信。” 他还举例:电话的确影响了写信的性质和频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比前者好。也就是说:新媒介并没有优于旧媒介,同时也不能取代旧媒介。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新媒介会破坏波兹曼所说的旧媒介所属的理性文明,而带来更多社会问题吗?
关于这个问题,梅罗维茨并没有马上下结论。他用了很多例子来作说明,比如电视的出现让女性从传统的家庭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开始了解和参与到社会发展中;又比如电子媒介使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界限消失,给了儿童提前体验成人世界的机会。他用大量篇幅的论述只是想说明一个观点:用新旧或好坏来对媒介做单一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形成误解,我们更应该把不同媒介带来的角色变化置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置于具体的场景中来看待。因为媒介并非天生好坏,道德和伦理的规范也受到场景变量的影响。
显然,梅罗维茨关于新旧媒介关系的看法褪去了锋利,更加偏向中立和温和。他更愿意用一种充满期待的态度去拥抱新媒介,因为在他看来,“新媒介被引入某种文化的同时会改变原有媒介的性质、含意和效果”,但这并非简单地替代,而且“当一个新的因素加入到某个旧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旧环境和新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全新环境……新环境总是胜于各个部分之和”。但同时,他也更加冷静地注意到了新媒介在不同场景中存在的不同问题,如“近几年中,酗酒、流产和自杀已成为‘儿童问题’”。也就是说,他更倾向于认为,新旧媒体的关系是一种融合,而非前者消解后者。它们彼此共生,在不同场景中发挥作用,从而不同程度和维度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2.戈夫曼的“区域”和梅罗维茨的“场景”的关系
梅罗维茨提出的“场景”概念,是对戈夫曼“区域”的引申,但与戈夫曼又不同。戈夫曼“区域”的定义是:“任何受到可感知边界某种程度限定的地方”。这个区域包含前台、后台,甚至有中台、侧台,其中,前台“指称特定表演的场所”。在他的论述中,“区域”更接近于物理区隔,人们在区域内的表演是面对面的。在本书中,梅罗维茨虽然把前后台的概念引入了关于场景的论述中,但是他也明确表示了自己与戈夫曼的不同:“戈夫曼的后区和前区行为模式描绘了一组静态舞台,它仅局限于面对面的交往上”,“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实际上,场景定义的讨论可以由直接物质现实问题完全转向只关注信息渠道。”可见,梅罗维茨赞同戈夫曼所说的“表演”,也赞同他关于“前后台”的讨论,但对“区域”概念本身,他认为只关注于物理边界不免有些局限。他的“场景”概念,克服了物理区域,对信息渠道给与了更多的关注。如他自己所说:“我们需要抛弃社会场景仅仅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面对面的交往的概念。我们需要研究更广泛、更有包容性的‘信息获取模式’观念。”这里所指的“信息”,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事实”不一样,它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所表达或传递或接收到的一种模糊信息,比如手势、表情等。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梅罗维茨和戈夫曼关于场景的看法不同,但并非前者对后者的全盘否定。在梅罗维茨这里,“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类。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
梅罗维茨注意到了场景里的人或信息流动并非完全平等,而是有“规则”。他提出:“每一个特定场景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人们,特别是有权势的人,能够定义新场景。”虽然他在本书中没有直接提到福柯,但是他关于“规则”的阐述与福柯的“权力”的观点有些相似之处。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而且这种权力并非暴力的残酷镇压,而是一种暗含着的知识权力。梅罗维茨也认为每一个场景都有规则,掌握信息的人就是规则的掌控者。
但同时梅罗维茨也提出:“某个个人在某个角色中的前区行为,不过是其他角色的间接的后区行为”,因为场景是不断变化的,在这个场景里的被规则者到了下一个场景里可能就成为了制定规则者。这个关于场景变化的观点戈夫曼也提出了,而且两人的看法几乎一模一样:“尽管人们倾向于把某个区域被标定为与某种表演相关联的前台或后台,但很多区域在这一时间和含义中是作为前台,而在另一时间和含义中却成了后台。”
场景除了不断变化以外,还能融合。梅罗维茨认为:“人们在不同的场景中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但是当两个场景融合后,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综合定义。” 可见,场景的融合并非1+1=2,而是达到了>2的效果。但个体的行为相加并不能产生社会现实,而是要依赖于不同场景中人们的行为,因为“社会现实并不是存在于人们行为的总和中,而是存在于所有场景行为模式的总体之中。”
梅罗维茨的“场景”概念,跨越了地域上的场景,将眼光投放到了信息流动的场景中,并察觉到了其中暗含的某种规则,不得不说,相比于戈夫曼的“区域”概念,梅罗维茨走得更远。
二、从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的变革
梅罗维茨认为,媒介变化导致了场景的变化,而场景的不同改变了我们对各种社会角色的认识。因此,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变革,也相应地引起了印刷场景到电子场景的变化。
他的这个判断不仅惹人发问:印刷场景和电子场景到底有何不同呢?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梅罗维茨上来就开始向我们解答这个疑惑。他提出,在印刷场景中的人们,并不能随便跨越到其他场景中,而是需要一定的门槛。因为“印刷编码的复杂在各种年龄群体内和群体间隔离了信息系统。要掌握印刷媒介中复杂信息就要求分阶段地学习,这造成了许多不同的群体,每一群体社会化的许多阶段,以及许多不同层次的地位和权威。”简单地说,就是书本信息并非人人都能读懂,懂印刷编码的人,既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才有准入权,而不懂这些信息的人显然被隔绝在外。但电子媒介不同,它“打破了印刷媒介所塑造出来的专门的、互不相同的信息系统。许多人通过电子媒介学习和体验到的东西,与他们的年龄、传统教育和社会地位相对无关。”因为电视信息的编码较书本简单,人们就算不识字,也能听得懂语言、看得懂画面。这个解释与他前边提到的“信息场景中的规则”的说法相一致。
除此之外,梅罗维茨还提出了电子场景和印刷场景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即:公开和私下行为的模糊。他认为:“电子媒介将过去人们直接而密切观察时所交换的信息也播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刷媒介具有‘前区偏向’,而电子媒介具有‘后区偏向’”。也就是说,书本只会传递较冰冷的文字信息,而电视兼具视听效果的特质,将人们面对面交流中所用到的表情、声音也传递了出来,而表情和声音的传递与文字传播是极不同的,前者更私密,后者则更正式。
两个场景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是:社会地点和物质地点的分离。在电子媒介之前,所有媒介的变化总会影响着地点之间的关系,但电子媒介改变了这种关系。就像梅罗维茨所说:“我们身体所处的地方不再决定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以及我们是谁。”这个观点与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伊尼斯把媒介分为偏时间的媒介和偏空间的媒介,前者如莎草纸,后者如黏土和石头上的文字。同时他提到:“印刷工业有一个特征:非集中化和地方主义。广播传播万里,覆盖广大地区,由于不受文化程度的拘束而打破了阶级界线,它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他们二人都看到了媒介之间的不同,即有的媒介让人们受制于空间或时间,而有的媒介却消除了界限。不同的是,伊尼斯更多从政治扩张来说,而梅罗维茨仅停留在社会文化层面。
电子媒介的诞生,给当时已经对印刷媒介习以为常的人们,确实带来了震撼和不安。“电子介入交往的结果,场景和行为的界定不再取决于物质位置……电子媒介将信息和经历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梅罗维茨的这句话,乍一看,似乎不好理解,但是想想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各地的美景、其他人的体验、暴力活动等,就明白了。从以前的空间受限、信息闭塞到爆炸式的信息裂变,人们接受它确实需要时间。
三、群体身份的变化
梅罗维茨在本书中提到的“群体身份”,或许也可用“群体角色”代替,他们是基于共享某个或某些信息系统而产生的。因此,“不同社会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多,不同‘群体’的数量也就越多。”电子媒介的出现,整合了信息系统,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群体身份的变化。
首先是后台群体行为的暴露。“电子媒介暴露了许多群体的传统的后台行为,过去只有群体成员才能获取的信息,现在群体外的人员也能得到。”这与前边他提到的电视传递了“表情”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去某些群体所特有的信息既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而现在,由于电子媒介的介入,这种优势不复存在。
其次是群体地点的破坏。“电子媒介对物质地点与信息获取之间关系的破坏,对群体身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女性,过去被限制在家庭区域内,但现在她们获知了更广阔世界的信息,这让她们的意识开始觉醒,并对传统的男女身份的设置进行了抗议。同样,电子媒介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原有的区域限制被消解,世界成为一体,成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
最后是高低身份场景的融合,使得权威被质疑。“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信息流的方向和模式而影响了传统的等级制度。”这一切变化主要来自于“后台的可见性”。因为“某人的物理位置和领地控制不再能确保对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信息控制”。梅罗维茨认为,高地位的角色常常依赖于对当时主要信息渠道的掌控,但如今信息的流动让这种权力弱化,普通百姓也渐渐掌握了一些渠道,故此,权威被质疑。虽然他前边提到任何场景内都有“规则”,都有“掌权人”,但是到这里他又认为“权力不再”,事实上,又脱离了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观点,因为在福柯看来,权力无处不在。
四、结论
或许是受作者所处时代的限制,本书中有些论述略显陈旧,尤其是第二部分的个别案例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梅罗维茨将戈夫曼和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进行的探索和尝试,无疑富有洞见。
试图简单地来将本书的观点描述为“媒介引起场景变化,场景变化改变了社会角色”的做法虽然并无不妥,但却略显单薄,因为梅罗维茨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对于媒介的思考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企图撬动整个社会秩序,找出媒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深层次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媒介的演化通过改变我们收发社会信息的方式重塑了社会地点和物质地点的关系,这就改变了社会秩序的逻辑。”
但是遗憾的是,对于政治的浅尝辄止和将社会的一切变革都归因于媒介和场景的做法,显然没有触碰到更深层次的原因,甚至或多或少表现出了对媒介的“过度崇拜”。当然这并不能掩盖梅罗维茨已取得的成果,毕竟人类历史的进程非一朝一夕之就,社会变革的力量复杂而多变,在这其中,媒介扮演了多大的角色,甚至将来会触发多大的变革都不得准确得知。媒介和人、媒介和社会的关系,仍需要我们继续艰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