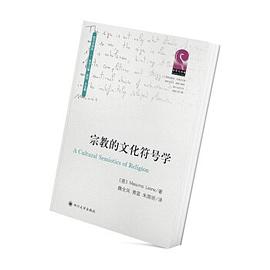
在《宗教的文化符号学》一书中,马西莫·莱昂内分析了意大利和其他城市宗教如何利用城市“符号域”有限的符号资源来激进地确认其独有的社会身份。马西莫·莱昂内认为,这种独有的社会身份具有很大的符号排他性,其不允许其他宗教对相同资源进行替代性使用。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资源日益严格且排他的见解,最终有可能导致欧洲宗教“符号域”的自我瓦解,从而限制大多数未来公民接触宗教意义与传播的可能性。因而,宗教文化的符号学家们必须及时提出新的知识假设,并且需要为促进更具可持续性的宗教制定新型“符号域”替代机制而努力。
宗教符号学的文化阐释
——评马西莫·莱昂内《宗教的文化符号学》
曹忠
书籍简介
作者:[意] 马西莫·莱昂内
译者:魏全凤、黄蓝、朱围丽
出版时间:2018年
马西莫·莱昂内(Massimo Leone)是意大利都灵大学符号学教授,词语与形象研究国际协会常务理事。其所任教的都灵大学有着厚重的符号学研究历史,著名符号学者艾柯就曾在都灵大学执教多年。作为都灵大学的一名符号学者,马西莫·莱昂内的研究延续了都灵大学源远流长的符号学研究传统,在宗教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以及视觉符号学等方面都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和著述。其著作《宗教的文化符号学》便是其文化符号学和宗教符号学研究方面的代表。
从书名上看,马西莫·莱昂内在《宗教的文化符号学》中终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教和符号的文化学向度上,试图通过文化学视野,多角度构建出宗教符号学的理论和实践框架。特别是其中利用“符号域”对宗教符号进行的文化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其运用符号学和文化学理论分析宗教现象的学术功底和开拓视野。
“符号域”一词最先由符号学者洛特曼提出。在其著作《思维的世界》一书中,他对“符号域”的概念做了详细阐述。洛特曼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语言都处于一个符号空间内,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相互作用,这个语言才能实现其功能。属于这一文化的整个符号空间,应当被视为一个符号单位、一个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
与洛特曼从语言学演化出的“符号域”概念不同,马西莫·莱昂内更倾向于“符号域”的生态根源关照。在马西莫·莱昂内看来,生物域——人类域——符号域的演进图谱,较好地诠释了生态学视野下的文化符号学演变路径。因此,源自生态学研究的“可持续性”概念也应当被文化符号研究所借鉴。但不论是洛特曼缘起语言学的“符号域”概念,还是马西莫·莱昂内根源生态学的“符号域”关注,都将符号的身份区隔以及“符号域”的可持续性作为考察核心。
在《宗教的文化符号学》一书中,马西莫·莱昂内分析了意大利和其他城市宗教如何利用城市“符号域”有限的符号资源来激进地确认其独有的社会身份。马西莫·莱昂内认为,这种独有的社会身份具有很大的符号排他性,其不允许其他宗教对相同资源进行替代性使用。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资源日益严格且排他的见解,最终有可能导致欧洲宗教“符号域”的自我瓦解,从而限制大多数未来公民接触宗教意义与传播的可能性。因而,宗教文化的符号学家们必须及时提出新的知识假设,并且需要为促进更具可持续性的宗教制定新型“符号域”替代机制而努力。
同时,马西莫·莱昂内还将“符号域”的身份区隔运用到宗教与语言的比较,以及后宗教社会下的仪式符号分析中。书中,他利用语言学中“识别群体成员行为”的希伯来词“示播列”,对语言学中的“阈值”进行阐释。在马西莫·莱昂内的论述中,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界概念,“阈值”是一种带有连续属性的“二维”区隔,在接近“阈值”的过程中,“数值往往会向一种平衡状态靠拢”。事实上,洛特曼就曾在“符号域”的论述中强调过符号的连续体特性。洛特曼曾言,在现实运作中,清晰的、功能单一的系统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只有进入到某种符号的连续体中才能起作用。此外,马西莫·莱昂内还利用洛特曼“符号域”考察了宗教文化中的“共同体”和“免疫体”概念。其中,“共同体”是指一种通过失去部分自我,剥夺部分自身身份,从而与他者建立关系的倾向。而且因为“共同体”可能使其成员处于具有传染性的联系中,因而“共同体”也被视为对成员个体身份的威胁(Landowski语)。为了克服这种威胁,现代社会不得不制定所谓的“免疫流程”:如果“共同体”推动个体自我超越,则“免疫体”会重建其身份,保护他们不与人进行危险的接触,免除他们将自身向他者性敞开的义务。
当然,这种符号的身份区隔和符号的连续性特质在后宗教时代的仪式行为中亦有体现。实际上,在仪式祛魅和日趋世俗化的后宗教社会,群体间的空间关系以及宗教仪式的连续体特性,已然成为人们在后宗教社会的世俗仪式中获得符号复魅的关键。马西莫·莱昂内还从大量民众在马约尔广场排队做集体瑜伽的现象,联想到排队这一世俗化行为在后宗教社会中涉及的仪式连续性问题。在他眼中,作为曾经宗教火刑场所的马约尔广场,其宗教仪式的公共空间特质在后宗教时代依旧以一种“潜文本”的形式得以延续。但他也敏锐地发现,在后宗教时代,完全的宗教艺术可能已被完全或者不完全世俗化的方式解构并重构。而且,人们虽然对神迹消失了兴趣,但依然在生活中渴望美学奇迹的发生。这种对美学神迹和崇高精神的追求,在马西莫·莱昂内看来依旧是“连续性”宗教仪式遗留在群体心中的“潜文本”所致。此外,马西莫·莱昂内还觉察到这种新旧仪式的交替会出现某种文化“缺口”,而且这种“缺口”往往被商业化的社会机构所占据,并以景观的方式销售给受众。
除了“符号域”这一视野外,马西莫·莱昂内在书中还引入了许多文化和哲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包括从宗教层面考察“绝对”概念的内涵,从符号学角度对“隐身文化”进行思考,从视觉研究视野对灵魂的符号学特性予以分析,从人类学范畴研究祷告的符号意义。同时,马西莫·莱昂内在书中还从运动性和“至上主义”等哲学视野出发,对文化和宗教的运动性及其演化的无限性,以及宗教意义哲学等进行了阐释。
对宗教符号学的文化阐释,无疑是马西莫·莱昂内《宗教的文化符号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实际上,正是这种从广阔文化视野考察宗教符号学的研究范式,使宗教符号学的研究摆脱了单纯的宗教思想解读,以及纯粹符号学的形式分析,并借助文化这一中介,实现了神性与理性研究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