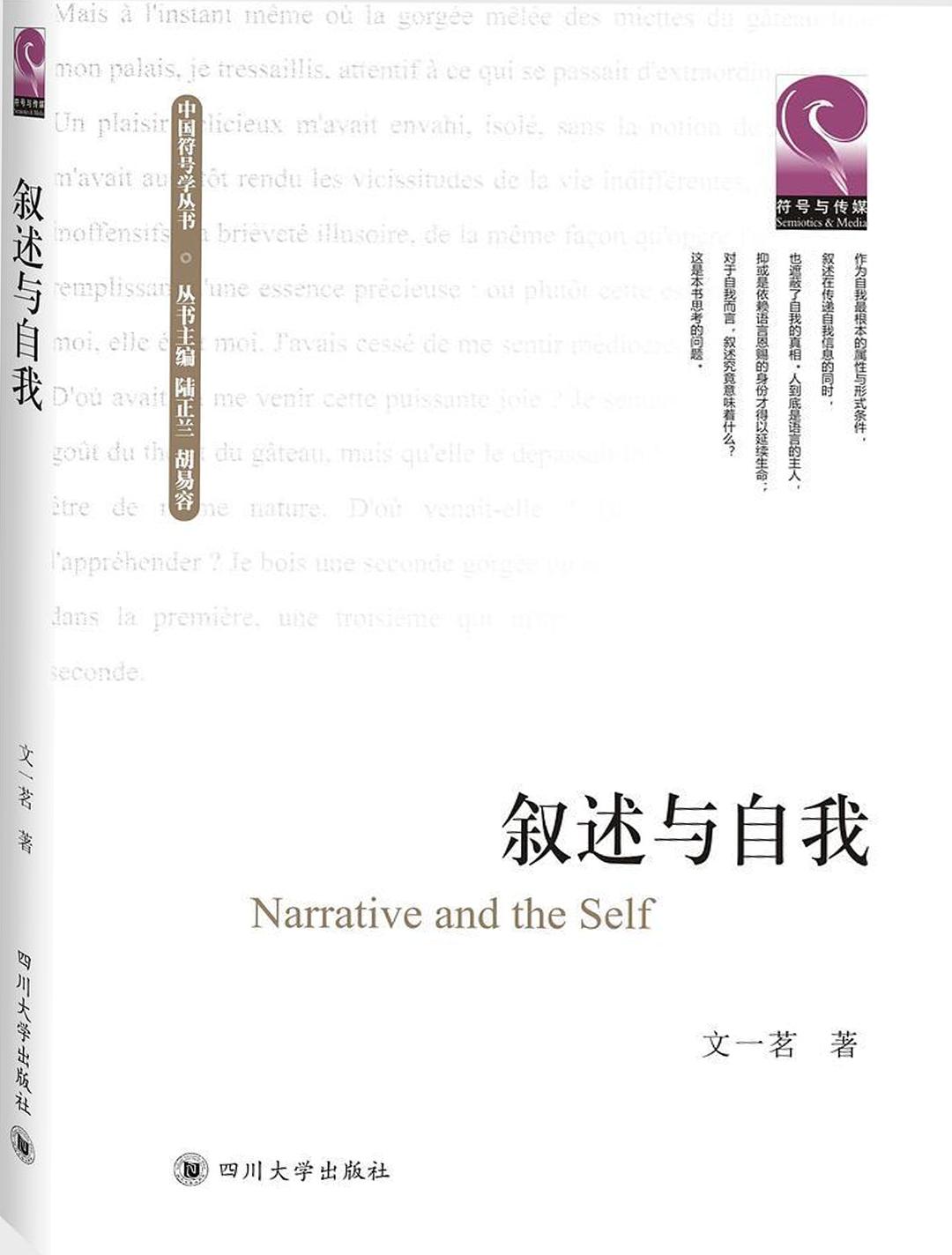
“主体”的秘密,似乎是一个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命题。自亚当和夏娃偷食“知识”禁果,“便开启了依照个体之小我,而非神的意志所区分的善恶世界”。然而,这个看似拥有着自我意识的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呢?在《叙述与自我》一书中,作者文一茗从自我的哲学转向含义谈起,把自我看作一个通过言说而形成的过程、“一种符号构建、一个意义过程”。基于此,文一茗从符号的角度,以“自我—符号—意义”三项式关联为钥匙,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叙述与自我”世界的大门。
张高珊评文一茗著《叙述与自我》
张高珊
“主体”的秘密,似乎是一个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命题。自亚当和夏娃偷食“知识”禁果,“便开启了依照个体之小我,而非神的意志所区分的善恶世界”(p. 5)。然而,这个看似拥有着自我意识的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呢?无论是启蒙时期完全自给自足的自我,又或是后现代意义上在语言中构建的“伪自我”,历史长河中,“自我何在”的探索,从未停止。在《叙述与自我》一书中,作者文一茗从自我的哲学转向含义谈起,把自我看作一个通过言说而形成的过程、“一种符号构建、一个意义过程”。基于此,文一茗从符号的角度,以“自我—符号—意义”三项式关联为钥匙,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叙述与自我”世界的大门。
从其表面框架来看,《叙述与自我》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理论·缘起”从自我的故事谈起,定义了自我的主体特性,即一种指涉自我,通过向他者的辐射,从而通达世界的话语能力(p. 6)。接着,作者详细借用皮尔斯符号三分法:再现体—对象—解释项三元关系(以解释项的无限衍义为论证核心),将自我代入叙述与符号化的语境中,探讨了符号的自我卷入叙述表意之路的理论逻辑。第二部分“推进·小说”中作者主要关注小说文本,探讨了符号自我在叙述过程中的分化、自反、以及与叙述主体、接受主体与文本意义的动态关系。同时,作者从文本的虚构性、情节以及元叙述三个方面谈论了说者自我经由叙述形式而进入文本内涵的路径。第三部分“类比·电影”中作者把视角再一次转换为电影文本,谈论了电影符号中主体的三分以及意义的获取。即电影文本是符号再现体的叙述主体,隐含意识形态下被询唤的观众是符号指涉对象的构建主体,而对电影二次叙述、形成元话语的主体则是符号解释项的释义主体。最后,在第四部分“文本·演绎”中,作者借用不同文本,升华了叙述与自我的思考:《时间中的孩子》深化了读者对时间的认知:不仅是叙述得以展开的符号载体,也是被赋予意义的对象本身。《踩影游戏》证明了文本,即符号示意,本质上的缺失焦虑:符号越多,暴露出来的意义缺失越多。《欲望教授》将欲望符号化,揭示了欲望的符号在自我存在之旅上的演变,以及自我渴望成为他者欲望的欲望的本质悲剧。《黑天鹅》则向读者展示了彼此否定的身份如何在符号自我中达到统一。最后,《玫瑰之名》揭示了符号示意的根本属性——无限衍义。
在通过对《叙述与自我》的仔细阅读后,本文发现,看似彼此分割、主题各异的四大部分之间,其实是一条从理论到实践到反思、环环相扣的逻辑论述,暗含着从“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探索——问题的回答”的深层逻辑。以“自我何在”为探索方向,本书仿佛一条自我与叙述的探寻旅程,而作者文一茗是带领每一位读者的导游,唱着《红蜻蜓》的童谣,手中持有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的旗帜,带领读者先后途经“小说”和“电影”两个场域,最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主体通过叙述,为自我找到了“待在”的栖居之所,在世界“迎着我的意向性产生的持续而充沛的意义之流中”(赵毅衡,2017,导论),凭借无限衍义的解释项,生生不息地产生意义。因此,本文以此为逻辑,分三部分(问题提出—探索—解答)论述本书的内在逻辑,对书中的理论与实践作简要探讨。
一、走进自我的叙述秘密:自我—符号—意义
本书一开始,作者以自己儿时喜欢的歌谣《红蜻蜓》为引,开启了主体对这个世界追问意义的旅程。接着,通过简单的一句话,作者巧妙地瓦解了自我意识的权威大厦。 “Three years’ experience as a salesperson enables m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在这个简历中常见的句式中,“我”感谢这三年的工作经历,感谢它成就了今天的“我”。通过这个例子,作者向我们说明,看似拥有着强烈主体意识的自我,其实只是“谦卑的受益者,并非发起行为的主体”(p. 6)。因此,作者揭示了主体存在的悖论:主体似乎总是陷于主动与被动之间,“总是通过控制与依赖而受制于他人”。通过纵观十几年的文学文化研究,作者发现了学界对自我的认知转向:并非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经验实体,而是一个通过言说自居的过程。而是“一种指涉自我、向他者辐射,由此通达世界的话语能力”(p. 6)。自我总是同时处于“说”与“被说”两个层面,通过叙述,自我符号化将自身建构为一个主体。在这种自我符号化的进程中,作者认为,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为这种意义的阐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打破了自索绪尔以来明确的能指—所指二元封闭意义系统。
以中国经典名作《红楼梦》中林黛玉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为例,作者正式将自我分析引入符号三分的场域。此句中,核心意象“残荷”是皮尔斯意义上的符号再现体(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符号),而林黛玉眼中凄凄惨惨的荷塘残叶是再现对象,更重要的,她体会出那一番独特韵味与丝丝惆怅则是意义产生的关键:解释项,进而“开启了新一轮的符号示意”(p. 8)。作者认为,在这样一个意义阐明的过程中,动态的“解释项”成为自我示意的关键,也为自我在叙述中的“待在”过程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保障。
皮尔斯将“解释项”精确的概括为“意指效应”(significance effect),即“符号再现体在解释者心中所创造的东西”,一种主体在接触符号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一种符号的“涵义”(significance),换言之,一种符号自身的转换与翻译,具备“无限转换”(endless commutability)的属性(p. 14)。而符号之所以为符号,就是因为其本身再现或者代表了某物。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解释项成为了一个原初符号,是主体下一轮释义的开始,这即是作者阐述的解释项的无限衍义属性:即每一个符号的解释项都会成为下一个符号的再现体。解释项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理解,而主体永远是一个随着符号释义之链向前无限滑行的谦卑主体。
因此,在这个探索真知、无限逼近真值的探索之路中,自我的秘密,本质上在于“自我—符号—意义”的三项式中。自我总是处于不停地感知、阐释、叙述、交流的动态过程中,将自己文本化,通过对过去我(对象)经验的整合,时刻追寻着未来我(解释项)的期望,在这个过程中,才得以成为“主体”,成为一个自觉谦卑的“符号自我”。换言之,主体就是在符号化进程中形成的自我意义。而解释项,作为一种无限衍义的话语延续,为自我的不断示意提供了基本的栖居之所。而意义本身,就是自我朝着完美的“终极解释项”挺进的过程。
经过上述探讨,作者从理论层面,向我们揭示了自我经过文本化叙述,无限逼近真知、探寻意义的过程。然而,在理论缘起之后,是作者在实践层面的思考。自我是如何在具体实践层面通过叙述而栖居的?叙述之内,自我何处安身?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作者引入了自我符号化的两个途径:小说叙述中的符号自我以及电影符号中的主体三分,进一步探寻了自我与叙述的关系。
二、小说叙述中的符号自我
基于之前分析,作者展示了“自我—符号—意义”三项式在把握叙述与自我关系中的重要性。至此,我们得知,自我只是处于“互动”中的话语能动性,而叙述行为,则是自我最根本的表意行为与存在方式。作为叙述中非常典型的一种话语行为,写作、或者讲故事本身也成为自我释义的重要一环。在一部小说中,形式本身就代表着文化,表层的文本叙述言说着说者的意图。因此,笔者发现,作者以叙述主体为切入点,以其三种分化为线索,进一步探讨了小说中的主体性问题。
作者认为,叙述主体是小说作者自我在文本层面的分化,是一个“随着文本叙述展开,而正在形成并确立自身的自我”(p. 62)。通过分裂成为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说者)多个视角,叙述主体携带着精心设计的符号编码与格局,包裹着明确的价值导向。然而,意义的终点却不仅仅只有叙述主体一方,而是一个“叙述主体意图、接受主体释义、文本携带信息三方之间来回试推的动态过程”(p. 62)。在这个过程中,叙述主体通过与接受主体对话,不断抛出的信息点,不断丰富其符号自我的内涵。而接受主体,从一定意义上,是叙述自我拟定的接受主体,是符号文本发出后遇到的另一个自我,是叙述主体以他者自居的自我。因此,在这种对话交互中,叙述主体是双层面的自我,一方面与接受主体(受述者)对话,一方面通过再复制一个自我,“在元层面与自己对话”。在这种同时存在的“叙述”与“被述”过程中,卷入叙述的自我一方面讲述“自我的故事”,一方面讲述“自我被构建的故事”(p. 69)。作者总结道,“叙述主体成为多棱镜中的影像,成为动态的符号自我,成为扑朔迷离,游离于文本发出与接受两端的‘隐含作者’”(p. 62)。此处,“隐含作者”特指在赵毅衡意义上文本身份引申所得的类自我,是作者自我在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分化。
然而,在隐含作者飘忽不定、游走在意义的发出与接受两端的语境下,自我究竟如何落实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回答到,任何的叙述都源于那个说事儿的“我”,即作者自我在文本层面的另一个分化—叙述者。以叙述者认知自我限制为切入,作者详细讨论了文本中叙述视角在隐性“框架”与显性“人格”之间滑动的三种可能性:框架叙述、人格叙述、以及人物叙述,从而论证了谁在看与谁在说的基本问题。而叙述角度本身,就是小说作者“选取”的某个特定的身份,来认知世界,是叙述者价值选择的指示,是一个符号化的自我视角,并“将其投射与认知对象的形象之中”(p. 72)。
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叙述者的不同视角,为自我的外部投射提供文本语境。与此同时,引语模式与话语权威,为自我的反思提供可能。通过分析小说文本中存在的四种引语模式,作者揭示了叙述者与角色之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话语竞争,从而分析了叙述主体在文本层面的第三次分化:角色(人物)。作者认为,角色本身,就是“自我文本符号化投射”(p. 94),而在不同情节中与不同说者“抢话”的过程,则体现了自我不同的存在模式。
更进一步,作者引入“元叙述”的概念,阐释了当叙述机制彻底暴露后,自我通过与文本世界分离而进行的反观与深入。叙述的“元化”,体现为叙述者的自我暴露、叙述机制的自我揭示、以及叙述意图的自我批评。在这种建构本身遭到揭露的情况下,“我”不仅在说,而且“深知自我为何言说、言说何物,并且在‘述说’的一刻,使自我言说的意义得以明确”(108)。简言之,叙述的“元化”所带来的,是自我的“元化”,以及自省的“元化”。正如作者引用所言:“我们赖以生存的,不仅是自我的故事,别忘了,还有一点更为致命——我们知道,自我是被叙述构建的”(p. 69)。
三、电影符号中的主体三分
在上述讨论中,作者在文本层面,讨论了自我在叙述层面的分化,重点关注了小说文本中“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从而为自我栖息叙述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紧接着,作者用电影镜头类比文字文本,关注电影文本中“看哪里”、“怎样看”、以及“看到了什么”的问题。以电影中最基本的视觉叙述单元—镜头为指示符,作者带领我们进入“电影”的世界,寻找自我存在的秘密。
类似于文字文本中的叙述干预,电影文本中的“镜头”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叙事单元,通过对元素的选择与规范,从而使得文本的传播与观影者的交流成为可能(p. 113)。在具体的电影文本中,镜头往往多种多样,根据拍摄距离,分为长镜头、中景镜头、以及特写镜头,根据摄影角度分类,又可以分为仰拍、俯拍和荷兰角镜头。各种镜头下确立焦点的方法也可以分为景深或者镜头的运动。然而,本书揭示出了这些复杂镜头后的本质:在电影这个视觉文本类型中,镜头以其特有的符号性,进行着更为隐蔽的叙述干预,而自我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世界陌生化,从而获得反观世界的能力与努力”(p. 122)。正如作者引用导演阿巴斯的话所言,镜头绝不来源于“固定在横冲直撞的牛角上盲拍的摄影机”,每一帧都是经过了选择,在这种选择下,本质的真实会暴露。
在谈论了电影镜头的基本功能以后,作者承前启后,通过进行文字文本与电影文本的类比,揭示了在文本叙述与镜头叙述中,自我符号化进程的差异。作者认为,“文字叙述重在‘塑形’,而电影叙述重在‘体验’”(p. 147)。因此,作者建议,我们将文字与电影叙述分别理解为意义的“内在化”与“外在化”文本。文字叙述是自我对世界的概念化还原(conceptual reduction),而电影则是一种自我体验的再现(experience representation)。然而,无论是“内化”或者“外化”,主体总是与示意彼此依存。因此,将电影看作一个自我叙述的一个符号,要理解其示意机制,就必须关注电影中的主体三分。
根据作者的分析,在电影符号中,电影文本是作为符号再现体的叙述主体(the speaking subject)、电影观众是作为符号指涉对象的建构主体(the spoken subject)、而意义则是最终作为解释项(the interpreting subject)的示意主体。首先,作者认为,电影文本的本质,在于其“双重缺席”的特性。演员在场时,观众不在。而观众在场时,演员不在。作为一个能指本身,电影是缺席的,而符号的意义,在于指涉缺席。因此,电影符号,是一种“双重缺席”,是一个缺席的符号再现体,使得接受主体(观众)的“自我认同在文化象征域和自我想象域之间来回替换”(p. 158)。故此,电影一方面是“我”所接受的,另一方面也是“我”所释放的。根据电影缝合理论(suture),电影文本召唤观看主体进入某个话语位置,“并以此赋予主体一种幻觉,即有一个稳定和持续的身份”(p. 159)。然而,作者揭示到,这种电影文本所召唤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完美和一个虚假的主体,因为观众能看到的,都是经过电影文本授权去“看碰巧属于另一人(且此人是缺席的)的目光所能企及的范围”(p. 160)。电影文本所暴露出来的,是其基于缺失主体欲望而展开的根本动力。对于观众来说,电影的示意在于观众发现自身缺失的那一刻,而电影符号本身指向“一种无限延伸,且不可弥补的欲望”(p. 161)。基于此,作者总结道,电影文本的意义,在于其抛出之后必然形成的二次叙述,即电影的元话语。正如在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人们将其还原为对自我而言别有意味的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样,通过电影叙述,“自我被包含在自己构建的画面中,使自我既外在于也内在于自我的画面中”(p. 164),最终见证自我的存在。
四、结语:叙述—自我的“待在”栖居
在前两部分的探讨中,作者分别在小说文本和电影符号的层面,对自我与叙述的关系,进行了实践与分析。至此,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自我利用叙述,将自己文本化,在不停地感知、传达、与叙述话语构建中成为主体。正如作者所说,“主体,是一个‘待在’的过程”(p. 60),而叙述就是主体“待在”的栖居之所,在这个叙述的家园里,自我在与外界动态的话语中,不断生成、更新。
而在一开始的引言中,作者有一句充满诗意的发问,“自我应该明了:叙述,哪里有尾声?文本,何曾有边际”(p. 1)。笔者认为,这无疑是一句伏笔,也是一种升华。是作者在将叙述具化为小说和电影后,启发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对于自我来说,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文本。尤其是在意义更加飘忽不定的后现代社会,叙述形式多样而复杂,自我“待在”的栖居之所,也在无形的扩大之中。自我存在的意义,也更加多元和丰富。正如作者借用对《黑天鹅》的分析,想要告诉读者的,当代社会语境下自我分裂已成为常态化。甚至彼此否定的身份都可以在符号自我中获得统一,而自我的终极意义,永远不会固定结束,永远在无限衍义的过程中。正如《玫瑰之名》所告诉我们的,自我永远在对意义(真相)无限逼近的旅途中。
参考文献:
文一茗(2019). 叙述与自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7). 哲学符号学.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