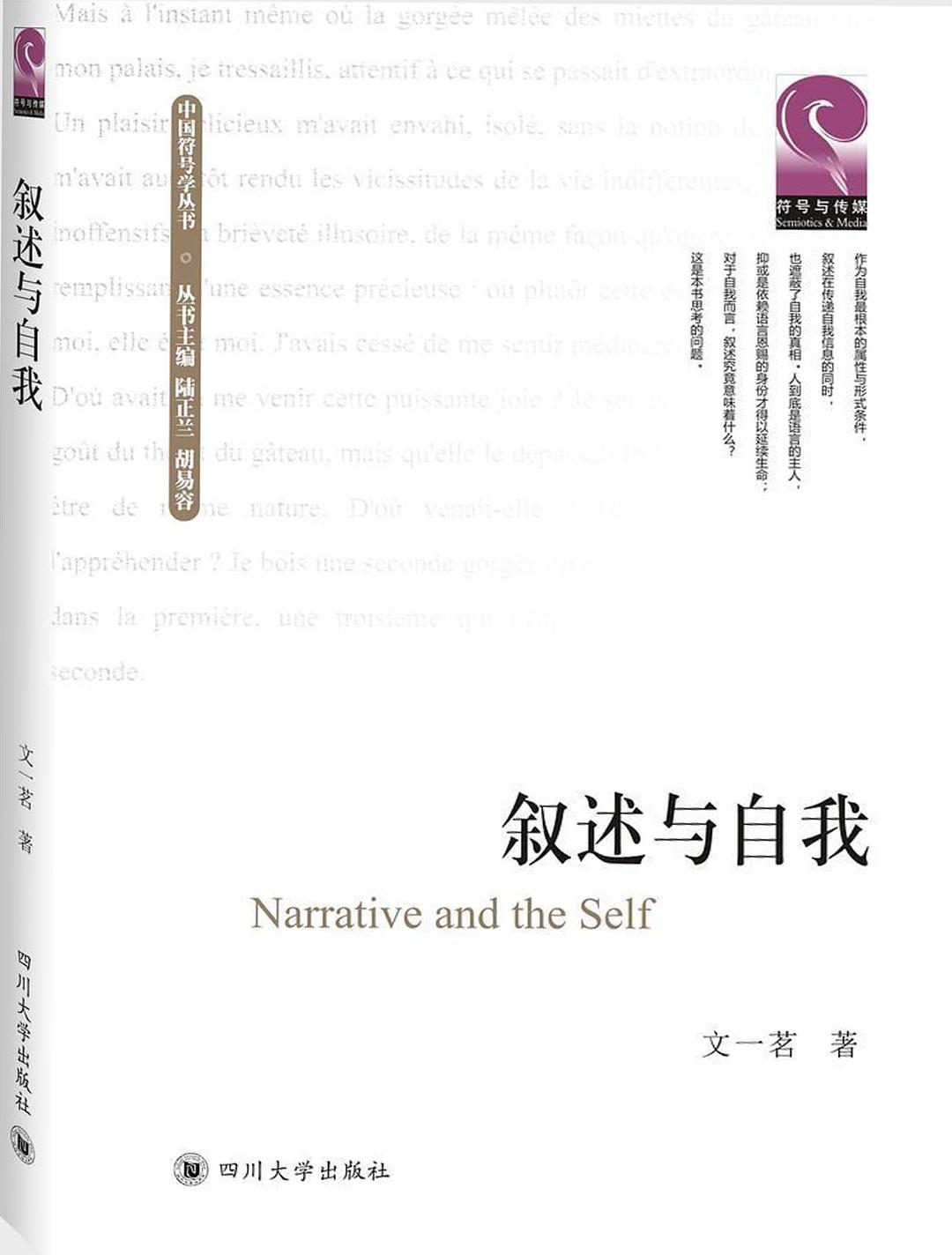
自我,不但是被说与被看的客体,更是承担着说与看的主体,即形象的来源。传统文本解读多聚焦于文本中呈现的客体集合,而忽略了形象的来源——主体。主体作为叙述行为的出发点,并不是既定存在,而是被叙述创造出来的一种时间产物,即是意识之源和自我之源,此时“我”并非彼时之“我”,自我不只是自我本身,而是不同时刻下意识自我的集合。
米会评文一茗《叙述与自我》
米会
自我,不但是被说与被看的客体,更是承担着说与看的主体,即形象的来源。传统文本解读多聚焦于文本中呈现的客体集合,而忽略了形象的来源——主体。主体作为叙述行为的出发点,并不是既定存在,而是被叙述创造出来的一种时间产物,即是意识之源和自我之源,此时“我”并非彼时之“我”,自我不只是自我本身,而是不同时刻下意识自我的集合。主体的这种时间间性使研究自我成为必要,而要想确定自我,就必须要回到人赖以存在的形式之中——叙述。自我之于叙述的意义,就如同苏菲的洞穴,自我在洞穴内,只有承载自我的主体才能知道,一旦踏出洞穴,就会被外界所感知。而叙述就像洞穴外的世界,是具体的可感的,它把抽象的自我代入具象的现实世界,自我由此得以现形。
一、引出生活之名——自我
作者文一茗在《叙述与自我》一书中,通过自我的缘起、推进、类比与文本演绎四部分层层推进,展开了对自我的辩护与追逐,表明自我不再是主体的绝对意志,而是指向言语的对立面和自我的缺失。作者通过自我的符号化过程揭示了自我与叙述主体、被述客体的深层关系,通过叙述主体和被述客体的悬置揭开叙述行为背后的映射意义,表明自我是借助叙述才得以通向意义世界,再借由意义到达自我。自我是客体,更是主体的不断演绎变幻,《叙述与自我》就像苏菲的“哲学信”,引出人类的终极命题“我是谁”的问题,然而答案不再是索绪尔的能指到所指的二元对应,而是自我—符号—意义的三项式关联,并借助意义实现对自我的认知。自我的符指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文本当中,而是通往现实世界的,凭借自我的符号生成过程和符号的自反性特征,使得现实中人对自我的实验成为可能。因此,《叙述与自我》这本书不仅是对自我理论的延伸,更是一部生活哲学之书。作者文一茗在《叙述与自我》一书中,扮演一位引路人,引领读者探索自我—发现自我—反思自我—重复自我—实践自我,由文本抵达现实,切入生活,道出人类生存的本质,即逐意的本能,同时为主体实验自我提供理论依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哲学生活之窗。
二、自我与言说的对望
人依赖叙述存活于世,并借助叙述这一形式传达意义,人对于意义的本能追求也使得交流成为可能,由此依靠意义与世界与他者与自我产生关联,从而构建关系,这样人就不是一座孤岛。但自现代以来,人不再是语言的主人,而反过来依赖语言所赐予的身份得以延续生命,在这场话语和主体的主权争夺战中,自我又该何处安身?文一茗在《叙述与自我》中提到,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已经退隐到话语当中,成为了话语的产物,对叙述的控制不再具有绝对意志。主体的权力被下放,语言占据了第一位,却使得叙述拥有了无限的自由和无尽衍义的可能。主体的存在是建立在潜在的“他者”之上的,在叙说的同时也在被说,执行看的任务的同时也在被看,这使得意义的自我增殖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在对主体进行言说的这一过程中,自我被同时卷入推进他者和暴露自我的两个过程当中,使得叙述拥有了双向意义和自反性特点。从而打破了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的二元封闭系统,示意结构从单向式结构演变为皮尔斯的三元结构,具备了无限转换的属性,同时引入了动态的解释项,使得主体无限接近真值。然而身处叙述当中的主体因为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叙述行为的动态变化,并不能完全看到自身,这使得自我具有一定的遮蔽性,在叙述行为结束之后,自我才完全显现。因此人对自我的发现往往是滞后于叙述这一行为的,如《踩影游戏》中艾琳的红蓝日记,在叙述进行时无论从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到接受意义来看都只是艾琳自我的一部分,而这种创造日记行为的对立面才是艾琳真正的自我,即对爱的感知和沉湎。“叙述作为一种动作,有开始和结尾,一个叙述行为的终止预示着一个自我的诞生和降临。”所以自我是在叙述行为完成之后才完全被看见,就像“有一天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你可能会突然停下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自己,就在你在树林散步的时候。”(p13)尽管符号是最根本的自我属性,却无法借此进入真正的自我,唯有将自身与世界拉开距离,才能开启自我指涉。因为任何文学叙述都指向自我的缺失而非圆满,而寻求意义的符号化过程,正是面对因缺失而导致焦虑存在的应对本能,所以叙述似乎成了一种使自我出离自身的离心运动。
三、自我与时间的悖论
作者文一茗开篇引用的一首童谣《红蜻蜓》,同样也印证了自我与自身的分离,揭示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之谜:“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见你那是哪一天?”跟随着叙述者笔下的时光印记,在追溯过往当中,当下“我”和过去“我”在某一时刻相遇,这种相遇究竟是简单的物理接轨还是电石撞击以后产生的的化学反应?文一茗在《叙述与自我》一书中给与了充分的回答:根据皮尔斯的三分论,当下“我”试图通过叙述这一符号化过程再现过去“我”,将自我根植于与自我的叙述交流图式之中,为未来“我”提供更多的方向和思考。但无论主体多么努力,得到的终究还是经当下“我”过滤后的自我,对自我的发现总是要追溯过往的缺失与不完满,过去和现在互为镜像,自我才显现真身。根据皮尔斯的三分论,叙述一旦开始,便开始了“说”与“被说”,所以主体在执行“说”这一行动的同时也在“被说”,看的同时也在被看,不仅体现了符号的自反性,也由此衍生出新的“自我”,呈现了“自我”的生成过程。人对自我的寻找似乎总是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中,作为语言行动的发出者,主体作为一个实体存在是可以凭借叙述(符号)超越时空的,而“自我”正是在主体这种超时空性中无限发展、衍变。由此观之,叙述之于自我的意义在于面对他者或自我解释自我的欲望或者被动解释。(p6)解释自我,对于主体本身而言,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寻,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和预告,任何叙述的目的都是使自我更为明晰地朝向未来。不管对于小说还是电影文本来说,自我作为一种符号性存在,都要借助叙述这一主要的叙事手段才能通向意义世界,叙述是我们跟世界交往的主要或者唯一方式,因此叙述不免带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属性,自我的意义也被无限延展。
四、自我在言语中的镜像化呈现
诺伯特.威利认为,自我作为一个充满社会性、对话性及自反性的符号,因而处于一个高度弹性化的阐释过程之中,是一个动态化的符号化过程。在时间上,自我分别处于过去、当下、未来三个符号化阶段,当下我通过阐释过去而为未来我提供方向。对应皮尔斯的三元模式,即从叙述—被述—新的叙述这一释意链条,将反思的自我置入他者的位置,自我意识成为自我关于自我的对话,不断生成新的自我。自我在这种示意的过程通过符号确立自身,而自我在行使能动性的同时,又将自己暴露为作为对象的客体,从而为主体示意打开了无限可能的空间。同时,自我示意的社会性、对话性、自反性的特征,也将自己包裹在身份这一社会性符号之中,人们借助身份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和不完满。如追忆往日的叙述,“我”可以将过去“我”与未来“我”统一于同一自我当中,身份成了对某种状态下的自我的命名,即主体对同一自我的认同,所以身份注定是自我的片面化而非完整主体的再现。(p27)身份的存在只是为了使自我变得可以理解,即使不能被完全知悉,也总会被不同程度地理解,所以身份实质上是自我和他者关于自我认知的一种再现和临时性表演。(28)如作者在此书的第四部分《时间中的孩子》这一电影文本中,通过“时间”和“孩子”这两个符号展现主体对已经失去的自我的寻找、对意义的追寻,“孩子”代表了主体对自我完满的欲望,与成人形成互为注解的两大符号,同时指向缺失的自我。时间在这一文本当中其物理属性被弱化,更大程度上成为了自我的命名,展现了主体对爱和被爱的追寻。
五、自我与身份的悖论
正是由于身份的同一性和叙述的交互性、自反性,主体的视域被扩大,文本的叙述层也更加复杂。叙述主体对自我的再现,总是指向主体的过去,将既有的自我形象作为再现对象,不停抛向未来那个待定的自我之域。由此观之,符号文本发出的第一个接受者总是另一个自我,在叙述文本层,它可以是叙述自我拟定的接受主体。所以,与叙述主体的分化相对应的也有接受主体的分化:隐含读者—受述者—人物。接受主体可以视作叙述主体以他者自居的自我,打破了叙述主体示意的封闭系统,使叙述主体成为多棱镜中的影像,成为动态的符号自我,给与自反性以无限可能。这样叙述主体的视域被扩大,就拥有更多自主权来玩弄文本,如由隐含作者引发的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 。作为一种叙述形式,不可靠叙述指的是一个文本中所承载的多方主体(叙述主体、读者接受主体及代表整个文本价值取向的隐含作者)意识之间的竞争与较量,以自反性为前提,印证了“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作者文一茗在此书第四部分的文本演绎部分,运用了小说文本《踩影游戏》对主体的这种权力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解读和分析。《踩影游戏》中女主人公艾琳的双重日记,吉尔的画作,瑞尔的创造性回忆,这三个文本环环相扣,形成了彼此生成、互为镜像的叙述格局。全书依次分化出了三个叙述层面:吉尔的画作是艾琳日记中的叙述分层,而艾琳的日记又是瑞尔虚构性回忆中的叙述分层,所以三个叙述层构成了一种画中画的效果。而小说的叙述者瑞尔作为一个冷眼旁观者,却又拥有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俯视父母的爱情故事,很明显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控制了整个叙述格局。小说最终通过“述”与“读”的行为,将爱表现为一种要求自我缺席的意义,展露爱的本质。由此看来,不可靠叙述的宗旨并非指向意义的不确定性,而是主体自愿放弃一部分权力让位于读者,交由读者解读释义,作者此时站在制高点俯视一切,故意制造理解障碍,使意义趋向多元化,模仿现实的可能和未知。因为意义是要达到未来的,而未来还未到来,一切皆有可能,借此打破现实和虚构的边界,体现符号定义的本真。
小结
叙述作为自我的主要栖居所,是行动元的集合,不管它是否同意,都要担负着再现自我和解释自我的责任,否则叙述就会落入虚无。但同时叙述又必须走出自身才能使自我得到揭示,自我总是指向叙述结束之后的不完满和缺失,不完满和缺失正是人对完满有预先的感知,所以才会有现在我和过去我的对视,对视的意图就是残缺的自我试图在未来我这里实现自我修复达到自我圆满,其本质原来是对自我的复制。博尔赫斯曾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先兆。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映像不会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有一次。”
参考文献:
(挪威)乔斯坦.贾德著,萧宝森译,《苏菲的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07。
文一茗,《叙述与自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10。
文一茗,《<红楼梦>叙述中的符号自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05。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09。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03。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