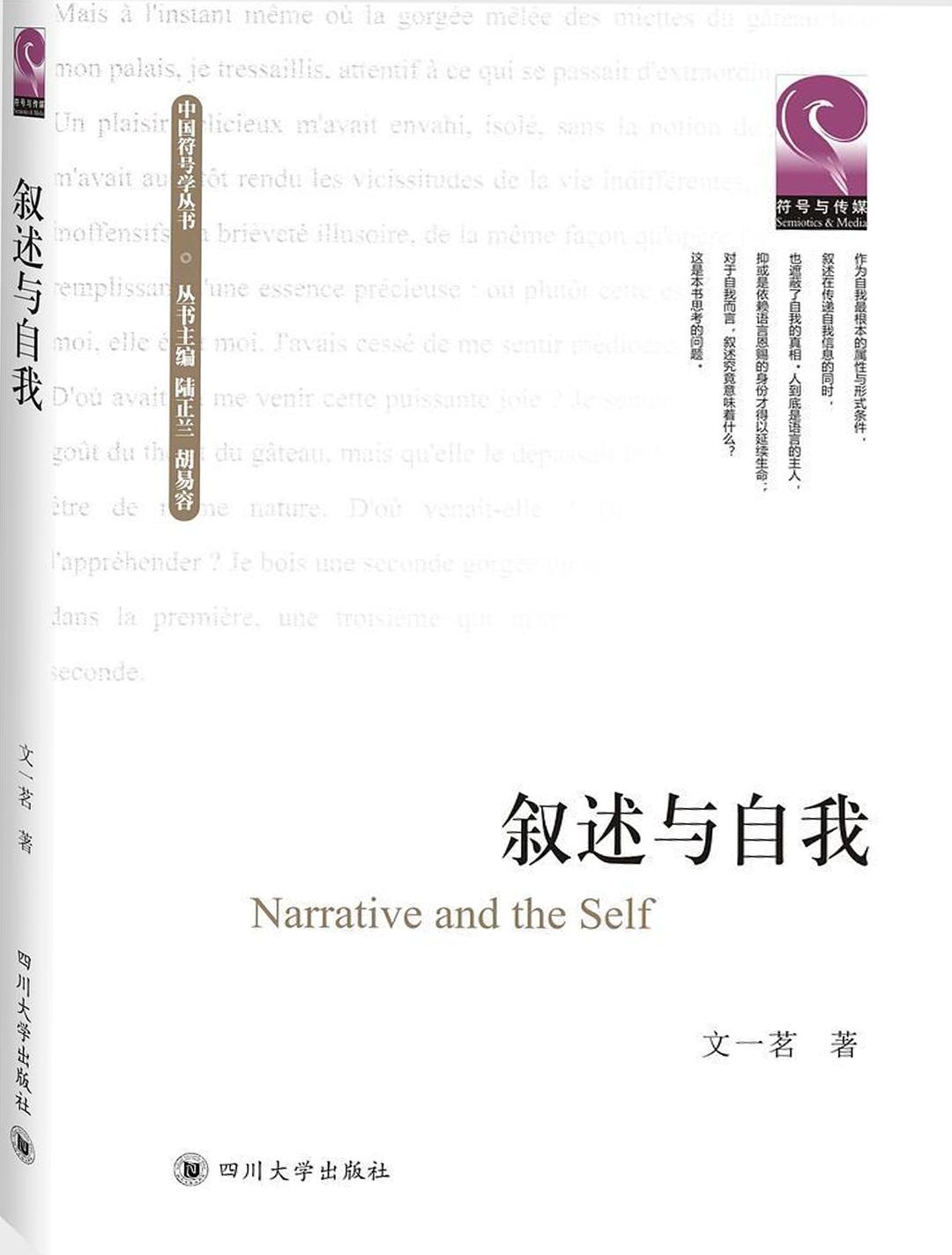
作者手持“自我、叙述与意义”三项式的钥匙,为我们叩问了自我的意义世界,也为我们探索自我的哲学奥秘做了进一步的努力。引言中,作者以颇具意味之言发问“叙述,哪里有尾声?文本,何曾有边界”,正如赵毅衡所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大文本,符号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美国符号学家诺伯特·威利在《符号自我》一书中也提到:“自我是一个符号(或者记号),这意味着自我由符号元素组成。”既然符号叙述建构了符号自我,作者便经由理论视域,再到文本推演,为我们挖掘了小说叙述及电影叙述中卷入自我的奥义。
陈超评文一茗著《叙述与自我》
陈超
何为自我?对于自我而言,叙述意味着什么?这是《叙述与自我》一书的鹄的。作者手持“自我、叙述与意义”三项式的钥匙,为我们叩问了自我的意义世界,也为我们探索自我的哲学奥秘做了进一步的努力。引言中,作者以颇具意味之言发问“叙述,哪里有尾声?文本,何曾有边界”,正如赵毅衡所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大文本,符号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美国符号学家诺伯特·威利在《符号自我》一书中也提到:“自我是一个符号(或者记号),这意味着自我由符号元素组成。”既然符号叙述建构了符号自我,作者便经由理论视域,再到文本推演,为我们挖掘了小说叙述及电影叙述中卷入自我的奥义。
一、叩问自我:自我、叙述与意义
在《叙述与自我》的“理论·缘起”部分,作者立足于皮尔斯“解释项”的意义机制,探讨了主体如何构建自我、主体如何追逐意义、自我如何示意以及自我、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等问题。
承载着自我意识的主体看似强大,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做主”呢?在正式的英文表述中,人作为主体的语法地位往往被刻意隐去,如此一来,“我”看似是行为动作的实施主体,实际上却是行为结果的承受者。那就意味着,主体本身存在悖论,即当主体采取主动时,它同时也是被动的,这是因为所谓的“主动”其实是主体“被迫”对遭遇之事做出反应。也即是说,主体看似掌握控制权,实质却因为依赖而受制于他人。
作者认为,主体拥有指涉自我、向他者辐射,并由此通达世界的话语能力。《叙述与自我》所提到的“自我”并非语言范式所坚持的“自我”,即“我”在说的过程中便隐退于“我”的话语之中,这里的“自我”通过言说而形成,它处于“说”与“被说”之中。经由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呼唤证实自我”模式,我们知晓,主体通过释意、达意与构意来暴露自我、卷入他者。正如本威尼斯特所言:主体性建立在语言的运用上,是指说者将自身定位为“主体”的能力。也就是说,主体是处在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自我”通过叙述(符号),将自身构建为一个“主体”。
在探讨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时,《叙述与自我》一书进一步强调了“身份”的重要性:主体在世,必然通过具体的身份来确定、展示并规范自我。正如赵毅衡所言,“自我必然以某种表意身份或解释身份出现,身份暂时替代了自我。”作者进一步指出,身份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主体自身的元语言,拥有解释自我、赋予自身意义的元符号能力。换言之,身份让我们在感知、行动时,能够知晓我们正在做什么,就好似感知、行动主体跳脱了原有行为,进而反观己身所为。如同哈姆雷特在“默然忍受命运的毒箭”与“挺身反抗”间抉择时,能够反观自己的处境。主体具有自反性,而身份则将这种自反性统一起来,如在追忆往日的叙述中,当下“我”可以将过去“我”与未来“我”统一于一个自我中,那么此时的身份就是自我的命名(符号化),但这样的身份不是完整的自我,充其量是自我的一部分或者一定条件下的自我。那就意味着,身份的每次达意似乎都是临时安排,而自我则可被视为所有身份的集合形成。
在自我如何安身的问题上,作者指出,自我栖居于叙述之中。任何文学叙述都指向自我的缺失而非自我的圆满,如此一来,唯有拉开自身与世界的距离,才能够开启自我指涉。然而,任何指涉都服务于一个“自己无法认识自身或世界”的叙述怪圈,自我在这一认知怪圈之中又分裂为“说”与“被说”两种存在形态,唯有叙述才能将自我置于自身的缺失上。正如作者之言,叙述之外,自我无处安身。自我总是通过叙述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恰如毕格尔之语“使我成为我的,不是意图、计划,也不是回忆,而是当下的行动,即写作”。有意思的是,叙述在开启自我的同时,也遮蔽了自我,这也印证了罗兰·巴尔特对自我言说的担忧“主体能够将各种不同的写作方式置于彼此对立之中,而唯独不能表达自己。”
自我、符号与意义又有何关联呢?叙述作为一个符号文本,也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那么“自我、叙述与意义”三项式,也可理解为“自我、符号与意义”。自我在不停感知、阐释、叙述、交流的动态过程中,将自己文本化,才得以成为“主体”,而主体则通过符号获得意义。换言之,符号是主体认知的必经路径,意义的获得是最终目的,主体则承载了经由路径、通达目的这一自反性过程。有必要说明的是,主体有所欠缺才需要符号,符号体现的正是主体所缺少的部分,而主体追寻意义势必采用符号,而符号越多就越显得意义之阙如,那么主体追寻的意义永远指向自身的有限性。至此,作者为我们建构了理论框架、厘清了理论视域的个中关系。
二、小说叙述:意义之域的符号自我
在理论上建构了自我、符号与意义的框架后,作者辗转来到小说场域,力图将自我置于意义之域,从叙述角度、引语情态模式、情节视域以及元叙述等维度为其寻找安身之处。
叙述的展开、接受是以落实叙述角度为肇始。叙述角度指向文本信息的流出,是符号文本建构及解读过程中最重要的指示符号,也为文本接受者指明了意义感知的方向。叙述角度具有自反性,指引着受述人的感知方向同时,也提供依据,让受述人反推叙述主体的认知取向。对于叙述角度的探讨,绕不开叙述视角、叙述态度、叙述距离等叙述主体意向性的形式问题的探讨,当然,最关键的是叙述者认知的自我限制问题,也就是叙述“框架—人格”的问题。赵毅衡在《究竟谁是“第三人称叙述者”》一文中提出来叙述“框架—人格”的概念,作者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叙述人称”重新界定,依据叙述者介入强度将其分为框架、人物以及人格叙述。小说文本中无论采用哪一类,或者组合其中两类或三类,都隐含了一个自反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做何种分类不是作者关注的核心,核心在于探讨不同程度的叙述干预,接受者可以反向“索骥”,追踪叙述者的目的所在。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叙述角度暗含多方主体话语权的争夺,那么对于叙述角度的区分最终指向的是符号示意中对自我意义的否定。
一个文本的展开就是一场无声的竞赛。从文本的隐含作者,到叙述者,再到角色都会以各自的方式争夺话语权,由此形成文本的叙述格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与角色之间的话语竞争,也即是,说者与被说者之间的话语争夺。角色能够做主,它能够反观叙述者作为说者的文本意图。角色的做主体现在角色与叙述者的话语对峙,也就是通过不同引语模式体现出二者的较量,而这种较量所隐藏的正是对主体性的的争夺。
情节是文本的骨架,也是文本的灵魂。作者认为,构成情节的三大叙述元素(角色、事件与时间)如同一张无边无际的意义网络,努力地展现自我的存在。由于一个角色只需要一个拟人格,所以我们常常“character”定义为“角色”而非“人格”。角色只需要为读者呈现一个“自我”符号,这是一个有能力与世界形成交流的能动性(agency)的“我”,当然,这样一个“我”需要借助“情节”才能展现其话语主体性。换言之,角色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话语主体,它可以始终保持沉默,却有其意义能力。而角色的意义能力,往往落实在事件的构筑上,而事件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角色意识到自我的“缺失”,由此展开弥补、回归、探寻, 最终以自我的方式为“缺失”赋予意义。此外,被卷入事件的角色,都会呈现出一个时间上的意义向度,这就是任何叙述的目的都在于使自我朝向更清晰的未来,正如萨特所言,对自我敞开的时间维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未来。
作者带领我们在小说的叙述角度、引语情态模式、情节视域,找到了“自我”的安身之所后,便立刻带领我们奔向“元叙述”,继续为自我寻找安身之处。所谓“元化”,就是通过分离得以实现自我的反观与深入。由于任何一种叙述形式成为主导,都会是对主题意义的暗示,那么,若元叙述在文本中占据主导趋势,也就体现出现代思想中一种非常突出的自我认知倾向,换言之,元叙述所体现的就是对原有自我的转向与突破。借由叙述者的自我暴露、叙述机制的自我揭示可知,元叙述体现出对自我的全面批评。文本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让“破碎的”自我栖居于此,而后现代的写作主张破坏意义的整体性,却因为断裂的意义与过多的身份,而将自我构成一种不连贯、不相关的多元性(multiplicity)。在此过程中,自我阐释的符号之链也沿着指示性与自反性无尽延伸。这也是为何后现代自我不会一次性被确定,而是不断处于阐释之中。元叙述作为后现代叙述形式之一,是对叙述权威的理性反思,元叙述文本中生成的自我,揭示出一种与读者对话的姿态。叙述者在坦白文本生成的过程中被“人物化”而被融于叙述情节之中,而这本身也被视为意义元素。元叙述消解叙述权威的目的在于要求读者退到文本之外,保持距离地思考文本。
叙述是自我在世最根本的思维活动,它无时无刻不折射出主体表达自我、了解他者进而把我存在的路径。在这一部分,作者借由小说叙述,挖掘了意义世界中的符号自我,换言之,作者在此将自我置于小说文本中,通过小说的叙述角度、引语情态模式、情节视域以及元叙述等维度进行推演,为自我找到了安身之处。
三、电影叙述:别有意味的符号自我
与小说一样,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也折射出符号与自我的内在联系, 在“类比·电影”部分,作者从电影镜头符号、电影背景音乐、电影蒙太奇、电影主体性等维度继续引导我们思考叙述与自我的关系。
镜头符号如何通过视觉语法实现对电影文本的叙述干预是作者引导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作者指出,电影必须具备虚构文本的文学性(诗意),观影者的视觉认知也必须以诗意的方式获得诗意的视觉理解(poetically accepted)。这就意味着,镜头需要打破日常视觉规则,成为观影思路的指示符号,也即是说,镜头需要引导观影者实现视觉陌生化。事实上,镜头确实能够通过控制拍摄距离、摄影角度、焦点等方面实现对电影文本进行叙述干预从而实现观影者的视觉诗化。
以拍摄距离为例,作者认为,中景镜头如同文字文本中框架隐身叙述,是摄像机的弱度干预;长镜头(定场镜头)则借由复杂充实的影像元素将“场景”本身对象化;特写镜头在提示我们注意“看到的”对象,也提示我们“看”的过程,从而,拉长了我们对影像元素的感知过程。无论哪一种都能对电影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从而获得陌生化效果 。从摄影角度来看,仰拍/俯拍镜头、荷兰角镜头、过肩镜头、侧面镜头等均是通过调整摄影角度,打破常规的中轴平视,实现叙述的干预,也打破了观影者的认知常态,延伸对角色和时间的理解,赋予对象独特的意义,亦能获得陌生化效果。除拍摄距离、摄影视角外,“有限性聚焦”的符号化模式也是镜头视觉语法对观影者思维之链产生作用的重要方式。景深(depth of field,DoF) 是确立焦点的重要语法,其布局打破视力常规的清晰区域,传递意味深长的人物关联或者叙述空间的新维度而使影像实现陌生化效果。镜头的运动是确立焦点的另一语法,是最常见的叙述干预,摄像机的位移是最直观的视觉指示符号,指示观影的意向,规范我们对影像符号的接受,如摇镜,将观影者的思维置于某种不确定中而实现影像文本的诗意化。
若从扭转常规的视觉语法来看,笔者以为广角镜头与长焦镜头对于空间透视的深度做到了极致,前者夸大空间深度,而后者压缩空间深度都会对电影的示意机制产生影响。由于镜头符号的示意能力始于对观影者思维的指示,如此看来,镜头叙述在本质上是一个引导观影者实现视觉陌生化的符号化过程。也就是说,电影符号对于思维的指示是自我将观影对象陌生化的同时,也将观影行为本身陌生化,从而使自我获得一种反观的能力。
跨媒介叙述中,一种叙述媒介与另一种叙述媒介的融合会使得该文本形成独特的叙述张力及认知效果。电影是集诸种媒介为一体的叙述文本,作者在这里引导我们思考了音乐媒介与视觉媒介之间的关联,即背景音乐在电影文本形成的“隐喻”关联,而这种关联的形成过程就是电影向观影者索取意义的符号化过程,也是电影符号示意的过程。作者认为,音乐文本诉诸于听觉感知,影像文本则依赖于视觉,二者融合形成跨媒介的感知路径,那么背景音乐使影像文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大大拓展了,如此便更能引起接受者的思考,进入联想和想象的的空间。罗展风在《必要的静默:世界电影音乐创作谈》中也谈及,电影音乐为电影注入更丰富的元素、信息,甚至更深刻的意义,也应当为影像注入另一层叙事语言。
电影作为符号叙述的文本,总归是要回到自我层面。作者强调,电影之于自我的效力在于对自我的拓展与延伸,从而向未曾涉及的意义领域推进。这就意味着电影音乐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音乐,而是与镜头“共谋”的符号化过程。镜头叙述使电影所指对象明晰,音乐符号则让观影者把所指对象与自己的体验情感,即思想融合于观影过程中,拉长从符号再现体到所指对象的距离,从而丰富电影符号对观影者的认知效力。从这个意义上看,电影音乐是观影者在接受电影信息时产生的一种自我延伸。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借助背景音乐来理解电影,而是借由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认知距离来理解自我、理解世界。
长久以来,学界乐此不疲地探讨蒙太奇应当被定位为一种构建方式亦或是被述元本身。从普多夫金到爱森斯坦,从安德烈·巴赞到让·米特里,从电影理论家到社会实践者均热衷于此。作者没有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而是将蒙太奇理解为一种风格来讨论其叙述功能。
如前所述,根据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上乘之作应当具备一种共同特质:一种可以使文本接受者面对世界,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的意义能力。而作者提出的“风格”正是这种文本示意的能力,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风格,而是一种特别的情感效力,使人游离于所接受的影像信息(符号所指对象),从而与符号文本产生最大程度的交汇与碰撞。作者提出,风格不只是叙述方式也是叙述本身,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风格本身是述与所述同时展开,是通过方式进入内容本身,若从观者的认知角度而言,风格则是方式与对象的总和。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作为“风格”的蒙太奇呢?作者从叙述蒙太奇、修辞蒙太奇、理性蒙太奇、镜头内蒙太奇四种蒙太奇探讨蒙太奇作为风格如何展现叙述力量。叙述蒙太奇通过“选择”传达叙述意图,让蒙太奇指向范围更大的意义空间,进而展现风格修辞蒙太奇,诸如隐喻蒙太奇、抒情蒙太奇关注影像元素的再现方式,即如何将观影者引入意义空间;理性蒙太奇展现了思维展开并构造对象的符号化过程;镜头内蒙太奇将运动与停滞、局部与整体诗意地整合于一体,而这本身就是自我认知的真实写照。蒙太奇对电影文本的干预是一种基于理解所进行的一种诗性的干预,干预的过程会促使观影者调整自我、丰富自我认知的可能性。将蒙太奇视为这样一种风格,也正是因为蒙太奇增加了电影文本的文学性。
主体在世的方式是通过不同途径进行达意与释意。将电影视为一个符号,就必须涉及电影中的主体问题。一个符号的符号再现体、符号所指涉的对象以及在符号指涉过程中生产意义解释项组成。该定义道出符号示意的本质特征在于:无限衍义的可能性以及主体的欲望与缺失之存在状态。作为符号的电影,也是由符号示意的三个方面组成,电影的意义永远在符号文本之外,游走于叙述主体、话语主体和阐释主体之间。电影文本的意义在于电影的元话语,也即是电影抵达观影者后必然形成的二次叙述。正如观影者在观影后将电影还原为一个别有意味的叙述、一个符号自我,在这个叙述中,自我被包含在自己构建的画面中,使自我既外在于也内在于自我的画面中,最终得以反观自我的存在意识。
在此部分,作者将自我与叙述的关系置于电影场域,借由电影镜头的文学性、电影音乐的隐喻关联、“风格”蒙太奇的文本示意能力以及电影的三分主体,探讨电影文本如何将自我进行延伸并推入别有意味的意义之域。
四、结语
概而论之,追逐意义是人之本质属性,这也是为何释意、达意与构意构成了主体最根本的三大经验活动,仿佛一切行为都在围绕意义进行,符号发出主体在符号文本上附上了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携带着意义,符号接收主体推演、重构解释意义。《叙述与自我》一书从理论框架的建构到小说符号文本乃至电影符号文本的阐释都在向我们揭示:符号、主体与意义彼此注解的“三位一体”式关系。自我在叙述的动态过程中,将自己文本化而成为“主体”,主体则通过符号获得意义,反过来充实主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符号是主体追逐意义的必经之路,意义是主体行之于世的最终目的,主体则是二者的承载之躯。至此,在作者的引导下,我们完成了一场经由叙述发现自我的意义之旅。
参考文献:
文一茗(2019). 叙述与自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7). 哲学符号学.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1).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威利,诺伯特(2011).符号自我(文一茗,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