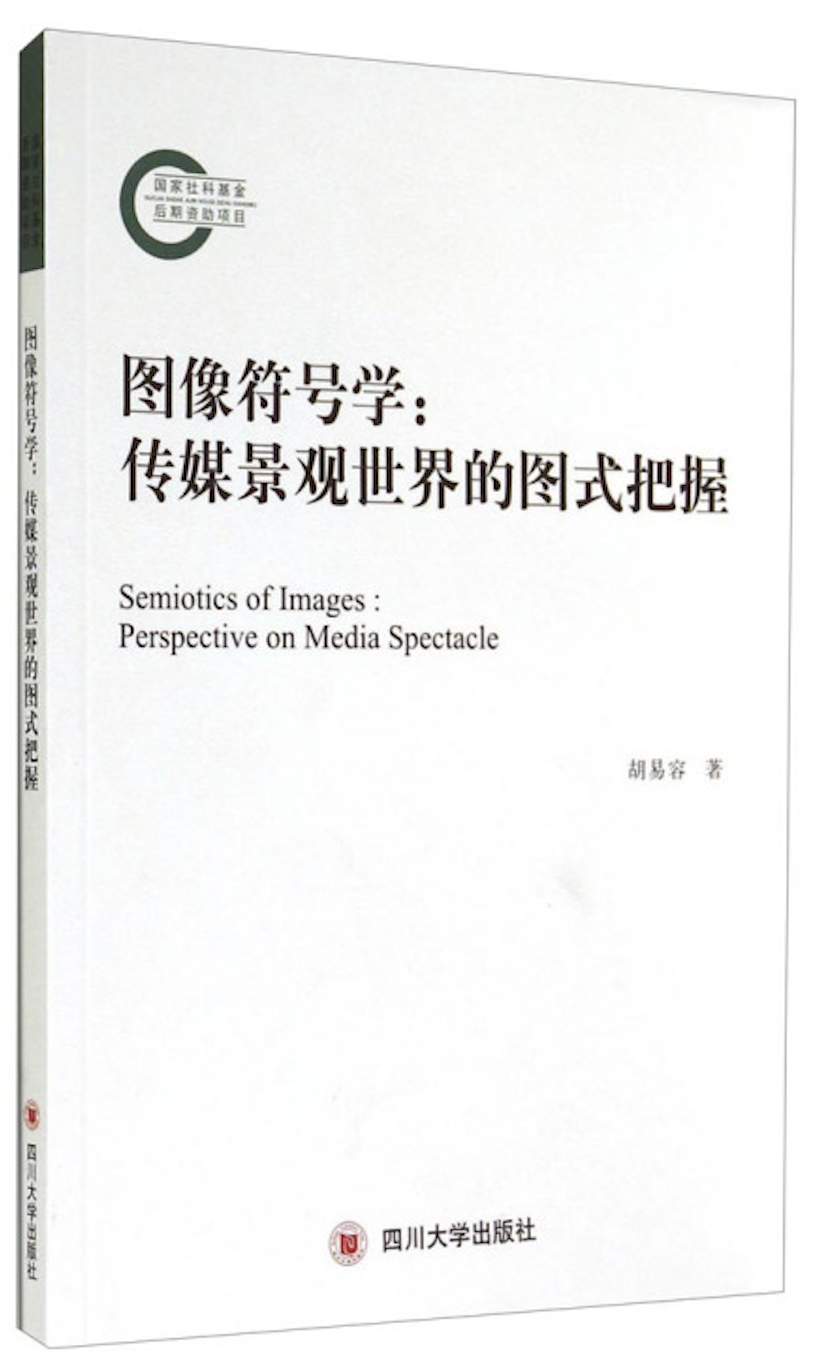
《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一书便是在潘诺夫斯基的圣像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当时潘诺夫斯基主要将研究对象界定在纯艺术领域,但随着当前传媒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击,社会精神贵族对社会总体的艺术垄断已然被打破,艺术成为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表意行为。泛艺术化使得图像学研究领域的限制被逐渐解除,图像符号学也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传媒景观世界。
黎静荷评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
黎静荷
一、图像研究分期与图像转向
在《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中,胡易容将图像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6世纪之前的“前肖像学时代”、16世纪至19世纪的“肖像学”(Iconography)阶段和20世纪以来由潘诺夫斯基所开创的“圣像学”(Iconology)阶段。
在学科分类体系并不完善的“前肖像学时代”,图像并不被当成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艺术或仪式的一部分被研究,这个阶段的图像研究主要基于人们生活经验来解释图像的母题或内容。而在16世纪时,图像阐释研究进入“肖像学”(亦译为“图像志”)阶段,肖像学分析要求解释者具备特定题材和概念的背景知识,用以解读画面中的形象、故事和寓言。在19世纪时肖像学研究达到顶峰,但是在参照宗教文献来解读绘画的阐释过程中,艺术逐渐沦为宗教文本的注脚,直到20世纪初,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创立瓦尔堡学派时,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瓦尔堡的弟子潘诺夫斯基开创了以研究符号性价值世界的内在含义来解读艺术图像的“圣像学”(iconology)研究,至此图像学研究开始逐步向“图像符号学”趋近,而潘诺夫斯基也被称为现代图像学的索绪尔。
《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一书便是在潘诺夫斯基的圣像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当时潘诺夫斯基主要将研究对象界定在纯艺术领域,但随着当前传媒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击,社会精神贵族对社会总体的艺术垄断已然被打破,艺术成为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表意行为。泛艺术化使得图像学研究领域的限制被逐渐解除,图像符号学也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传媒景观世界。
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方式的转型使得图像在现代社会变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准确地概括这种变化,图像理论家米切尔(W.J.T.Mitchell)提出了“图像转向”的概念,并开始在文化研究中强调对日常生活图像的解读。但“图像转向”并不只是一种图像规模和数量的膨胀,也并不仅限于日常生活图像的理论化解读,从根本上说,图像理论是人类社会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将“图像化”的世界观视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这种表现的关键不在于现代世界所生产的图像数量,而是现代社会发生自我认知的特有方式,即图像作为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的基本方式而存在。在图像转向之后,世界不再作为一个文本被理解,而是作为一种图景被观看,而“观看”也作为关键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取代了以往的“阅读”,我们无法再将语言学转向阶段的符号观念毫无变动地运用于图像之上了,至少在现在这种垄断的权力已然松动。
二、图像的家族谱系
在本书中作者将图像定义为以人类视觉经验为原型,以像似性为基本特征的意义知觉形式(包括视觉的比喻、引申形式)。根据定义,图像的谱系可以被分为物理对象、官能对象、人工代码和认知模式四类,每一类的两个子类分别为其“基础形态”和“延伸形态”,如物理对象可以被分为可见物和不可见物,二者分别为物理对象的基础形态和延伸形态,而联觉与幻象、视图与语象、形象与景观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作者的分类是基于图像理论家米切尔的分类而作的,他们都试图从图像的外延入手,从图像的谱系序列中寻找其内在特质,但不同于米切尔依据不同学科话语对“image”概念所进行的松散划分,作者更倾向于从认知图式和媒介方式本身来建立图像的家族谱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树状图的起点将图像标示为“图式经验”,其中“图式”一词来自康德,意指一种基于人类先验的范式,它是知识经验与对象交割的中介,属于人类总体经验的范畴。而“经验”一词则将图像的范畴严谨地框定在人类感知与意义解释层面,强调图像并非一种自明的对象物,而是一种人类经验范畴的概念建构方式。
三、符号学视域中的图像研究
这种对图像阐释维度的强调与作者倾向意义解释的符号学立场是相符的。作者认为符号与信号最关键的区别正是符号意义阐释的开放性,不同于信号对过程性要素的强调,符号注重解释而倾向于接受者的感知。作者表明虽然符号学界因理论体系的差异,对符号的理解多有不同,但符号的释义性特征正逐渐成为现代符号学研究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对皮尔斯、艾柯等学者“以释义为中心”的符号学概念之上的。
在阐释图像概念时,作者强调图像之所以成为图像,是因为观看者以“图像的方式”感知和理解它们,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与皮尔斯的名句“释义之所及,符号之所在”(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的逻辑是相通的,在图像研究中皮尔斯的观点可以被拓展为“nothing is an image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n image”。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观看者与阐释者,图像就不再成为图像了。作者所关注的一直都是作为有待被接受者解读的符号而存在的图像,而不是自明的、客观的、脱离阐释者的非符号对象,这种符号学视域下的图像研究大大拓宽了研究对象的边界与阐释的限度,为解读传媒景观世界丰富的视觉材料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