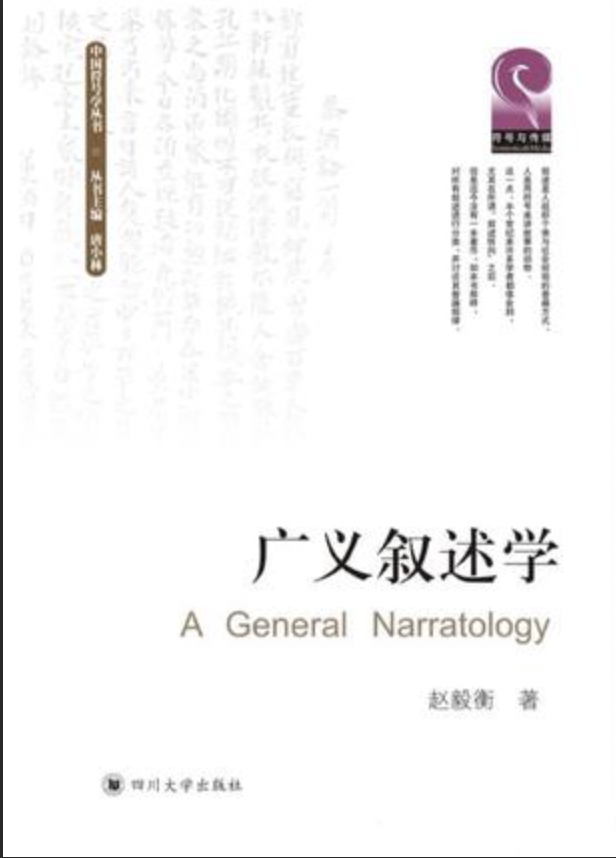
叙述学在经历了经典叙述学、后经典叙述学两个阶段后,迎来了“叙述转向”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叙述学的发展亟需一套适用于所有叙述的广义叙述学体系。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突破了叙述学以往局限于小说的研究范围,把其他诸如电影、广告、游戏等叙述门类纳入叙述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几大重要问题的论述,为广义叙述学构建了一套理论框架。
李胜男评赵毅衡《广义叙述学》
李胜男
叙述学在经历了经典叙述学、后经典叙述学两个阶段后,迎来了“叙述转向”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叙述学的发展亟需一套适用于所有叙述的广义叙述学体系。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突破了叙述学以往局限于小说的研究范围,把其他诸如电影、广告、游戏等叙述门类纳入叙述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几大重要问题的论述,为广义叙述学构建了一套理论框架。
一、《广义叙述学》的内部逻辑与结构
要建立一门广义叙述学,首先需要对各类叙述体裁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讨论所有叙述体裁的共同规律。叙述的体裁丰富多样,以什么标准进行划分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赵毅衡在前言中阐明了他分类的依据:纵横两条轴线。其一是根据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划分为纪实与虚构两大类;其二是根据媒介—时向方式,适用媒介分为记录类、记录演示类、演示类、类演示类与意动类,时间向度分为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类现在、未来五种类型,分别与媒介分类一一对应。
正文中对于叙述各体裁的讨论完全基于这个分类模式,聚焦纪实与虚构两大类型的叙述,兼具对于纪录类、演示类、意动类叙述文本的探讨。因此,作者在前言部分通过表格直接列出叙述体裁的基本分类,为后面正文的讨论做出了铺垫。
《广义叙述学》的正文包括导论和四个部分,由浅入深地探讨了所有叙述的普遍规律。导论部分回答了关于广义叙述学的几个关键性问题。首先,为什么一定要建立一门广义叙述学。建立广义叙述学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叙述之于人的重要性。“叙述是人生在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还在于叙述学的发展缺乏对于广义叙述的讨论,这个问题源自叙述学内部“体裁自限”,长久以来,叙述学的研究局限于文学叙述之内。因此,建立一门广义叙述学不仅是叙述学学科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探寻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
要建立广义叙述学,就需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叙述上。如果不厘清叙述的定义,那么就无法为广义叙述学的研究划定清晰的范围。“叙述转向”的背景,使得叙述的定义更加复杂化。原先不认为是叙述的体裁,纷纷转向叙述,要研究广义的叙述学,必须给出一个判断文本是否是叙述的标准。作者结合瑞恩和瓦尔特对于叙述的定义,提出叙述的“底线”定义:叙述文本必定包含两个叙述化的过程,第一有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第二该文本从接收者的角度,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
作者通过四个部分,从叙述的分类引入,讨论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叙述中的时间与情节问题以及叙述中的主体冲突。要讨论广义叙述中的重要问题,不可回避地还是要先从不同类型的叙述体裁开始。只有明确各类叙述的特点,才能发现其中的共同规律。
第一部分继续前言中对于所有叙述体裁分类的讨论。作者选择了意动类叙述、演示类叙述、心像叙述几个类型进行细致地分析,并且着重探讨了纪实型和虚构型两大叙述的区分。在分析以上几类叙述前,作者先讨论了文本意向性的问题,文本的意向性与文本的分类息息相关,是叙述文本分类的原则。同一段描述,在意向性不同的叙述体裁中,意义完全不同。而作者在前言提出的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以及媒介-时间向度仍然是作者划分各种叙述类型的标准。根据媒介构成的品质叙述可以分成记录、演示以及意动三大类,作者分别对这三类的叙述的特点进行了讨论。而从再现本体地位类型区分出来的纪实类与虚构类两大叙述是不仅是叙述学内部的难题,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课题。对于纪实与虚构的区分,作者先讨论从风格、指称性区分的可能性,而后创新性地提出“区隔框架”来区分两类叙述。纪实型叙述只有一层区隔,而虚构叙述存在“二度区隔”。
对叙述进行分类后,紧接着就是叙述如何构建的问题。在第二部分,赵毅衡分别从叙述者的角度、叙述文本接收者的角度以及底本与述本的角度来探讨了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谈到叙述的建构,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叙述者建构了叙述。综合各种叙述体裁来看,叙述者呈现两种形态,要么是具有人格性的个人或人物,要么表现为叙述框架。不论是哪一种,叙述者在叙述文本构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并不只有叙述者参与了叙述构筑的过程。这就涉及到作者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二次叙述化”。在一次叙述化的过程中,叙述化在文本中加入叙述性,把一个符号文本变成叙述文本。但叙述文本的构筑并不止步于此,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第二次叙述化的过程。只考虑叙述化便把接收者对于叙述构筑的贡献排除在外。文本的构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并不定型于叙述文本生成之时,而是在传达的过程中不断建构的。
对于叙述来说,情节这一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从作者给出的叙述定义也可以看出,“人物参与事件”是叙述定义的底线。那么叙述的情节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关乎叙述构筑的重要问题。叙述学界长期存在对于底本与述本关系的探讨,各学者之间存在较大争议。赵毅衡突破性地运用符号学中符号双轴的理论去厘清底本与述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叙述文本同其他的符号文本一样,都是在聚合与组合两个轴上进行操作的。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就是选择和组合的关系,而叙述就是在选择中产生的。底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选项,述本把被选中的符号组合成叙述文本。
作者给出的叙述底线定义中,叙述文本必须被接受者认为是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的。因此叙述的时间问题也是探讨广义叙述学不可避免的问题之一。叙述中涉及到的时间十分复杂,包括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文本内外时间间距以及叙述意向时间四个范畴。当被叙述时间一直延伸,在某一时刻会与叙述行为时刻重合。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就会出现“二我差”。尤其是在成长小说中,二我走向合拢,反映出人物的成熟。情节的问题更为复杂,首先是情节与事件的区分。导论中已提出,情节是叙述的底线定义,而事件则不一定发生在叙述之中。此外,还涉及到“否叙述”以及“另叙述”的问题。在纪实型和虚构型两大叙述中,“否叙述”的地位是不同的。因此,也可以成为区分这两类叙述的一个标准。结合上一部分对于述本与底本的讨论,作者得出结论,叙述的情节是由叙述者筛选可叙述的事件形成的。这种选择要受到社会规约以及叙述体裁的两种限制,并且要考虑接收者的兴趣以及是否完成叙述体裁的功能。
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聚焦叙述文本中的主体问题。“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两大问题,是叙述学的热点问题。赵毅衡把隐含作者这一问题的讨论延伸到“普遍隐含作者”上。首先从叙述中的伴随文本开始分类进行探讨。叙述文本和其他符号文本一样有伴随文本,伴随文本体现的是文本与世界的联系。任何文本,都必然携带大量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这些内容不一定并且通常不显现在文本中,更多隐藏于文本外。但要解读文本的含义,伴随文本是必不可少的。作者分类讨论伴随文本之后,紧接着提出“全文本”的概念,不同体裁的文本,对于伴随文本的整合能力是不同的。“全文本”帮助确定文本的范围,而明确了文本范围,才能从中归纳出“隐含作者”。广义叙述学的目的之一是帮助叙述学走出“体裁自限”的困境,因此,在“隐含作者”的问题上不能局限在小说中,必须扩展到所有叙述体裁的“普遍隐含作者”。通过“全文本”的概念,确定文本的范围,从而归纳出小说以外其他叙述体裁的“隐含作者”。在“不可靠叙述”这一问题上,作者仍然是加入了文学叙述以外的其他叙述体裁的讨论,例如纪实型叙述的可靠性。并且进一步总结了不可靠的类型,阐明了如何去识别全局不可靠以及如何修正局部不可靠。
二、广义叙述学与符号叙述学
赵毅衡在导论部分给出了叙述文本的定义,同时对比了其在《符号学》一书中对符号文本的定义。与叙述文本不同的是,符号文本很多是非人工制造的,没有发送主体的“自然符号”。虽然两者之间存在区别,但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赵毅衡指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一旦符号文本描写人物和变化(即“情节”),就是叙述。叙述文本在符号文本中的比例极大。卡特、恰特曼等学者也指出符号学对于研究叙述问题的重要性。
符号叙述学研究的对象是“叙述性”。和其他叙述学不同,符号叙述学研究范围超出了小说以及电影,它关注各种符号文本中的叙述性。正因为符号叙述学克服了传统叙述学“体裁自限”的问题,使得广义叙述学成为可能。所以可以说广义叙述学就是符号叙述学,要建立广义叙述学必然需要符号学的理论。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的讨论当中,多处通过符号学的视角去分析叙述问题。
(1) 叙述接收者参与叙述过程
在正文第二部分论及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时,除了叙述者以及文本形成过程的叙述化之外,赵毅衡还提出“二次叙述化”的概念。一次叙述化,发生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在一个文本中加入叙述性,把它从一个普通的符号文本变成叙述文本。但叙述的过程并不止于此,除了文本构成的过程,文本传达、接收的过程也是叙述文本建构的过程。赵毅衡指出,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为叙述文本。
赵毅衡提出的二次叙述化参与构筑叙述文本,体现出对叙述文本接收者以及其给出的解释意义的关注。在符号过程中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发送者的意图意义,符号信息携带的文本意义,以及接收者的解释意义。在不同的符号文本当中,对于这三种意义的重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科学性的文本重视符号本身的文本意义,实用性的文本侧重文本发送者传达的意图意义,而在文化交流的文本中,往往解释意义更为重要。二次叙述化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回顾叙述文本中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追溯情节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叙述文本的接收者去解释文本中的情节。
对于任何一个符号而言,皮尔斯认为可以将其三分为再现体,客体和解释项。索绪尔的二分法将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两部分,基本可以对应皮尔斯的前两项。符号的第三元素解释项至关重要,正因为有它,任何符号必须有接收者。相应地,叙述文本作为一个有情节的符号文本,也必须有其接收者。既然叙述文本存在接收者,那么接收者对于叙述文本的解释也必然参与了叙述文本的构建过程中。
正如符号意义的生成不是在发送符号后便截止了一样,任何叙述文本都不是处于已经被构筑完成的状态。叙述文本的构筑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生成、构建的动态过程。
(2) 双轴理论看底本与述本问题
底本与述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起源于叙述学界对于分层理论的批判。很多研究者支持一元模式,即只有述本而无底本,反对双层结构论。但赵毅衡指出,底本实际上更为复杂,先前的研究并没有厘清底本与述本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提议,从符号学的角度也许会对底本的研究有所启发。
在符号学当中,符号文本有两个展开的向度,一个是组合轴,另一个是聚合轴。赵毅衡认为,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必然在这个双轴关系中展开。作为具有情节的符号文本,叙述文本也是通过符号表意的活动,因此存在使用双轴关系来考察叙述文本的可能。
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形成,就隐藏起来;而组合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必然是显现的。因此,符号表意的过程,逻辑上必然是先从聚合轴的运作开始的。首先在聚合轴进行选择,然后才能产生组合。当文本完成之后,显现的部分属于表层结构,而聚合在文本完成后隐藏在背景之中,属于深层结构。如果用双轴理论来看待底本和述本的问题,就能回答底本和述本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以及在叙述文本的生成中底本和述本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
从逻辑上来看,叙述文本的生成过程也是始于底本的聚合操作,然后才进入到述本的组合中。底本作为叙述文本的“聚合轴”,本质就是诸多可供选择的选项,因此述本中的所有成分都来自底本,只不过显现的只有被选择进入叙述文本的部分。整个述本,都是与底本“双层叠合”的。叙述文本中情节的产生,就在于选择当中。底本提供的选择不仅仅是文本的内容元素,还包括其他所有述本需要的元素。既然所有符号表意行为都需要在双轴中进行,那么所有的叙述文本也必然都需要底本和述本进行聚合与组合的操作。这也就进一步回答了一些学者对于纪实型叙述底本述本的疑惑:纪实型的叙述同样存在底本与述本。底本是有关事件的全部材料,通过选择显现在述本中,重构这一事件。
通过使用符号学双轴理论对于底本与述本问题的分析,理清了两者间的逻辑先后关系,以及两者对于文本构成发挥的作用。并且,赵毅衡也通过以上的分析,肯定了叙述文本的分层结构。
(3) 伴随文本与隐含作者
在广义叙述学当中,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归纳出体现其意义-价值观的隐含作者。对于寻找隐含作者来说,确定文本的范围至关重要。文本的接收者能够感知到的,除了文本之外还有一部分的伴随文本。而符号文本的解释,需要理解文本与整个文化的关系。
在符号学中,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与联系就是文本与整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在符号文本中占极大比例的叙述文本,同样不例外。因此,在解读叙述文本时,也必然考虑其携带的伴随文本。文本接收者从中归纳出隐含作者的努力必然离不开对于伴随文本的理解。甚至,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
赵毅衡在其《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把伴随文本分为三类:显性的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和型文本;生成性的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和同时文本;解释性的伴随文本,包括评论文本、链文本以及先后文本。在《广义叙述学》中,对以上三类伴随文本也进行了较为细致地介绍,并阐明它们如何作用于叙述文本的解释。但在广义叙述学中引入伴随文本的概念,更多的是为“全文本”这个概念作铺垫。“全文本”指不同体裁的文本,对于伴随文本的“整合能力”不同。文学类的文本因文本本身携带的信息量较多,因此副文本等伴随文本都不能算文本的一部分,反过来,图像、音乐等媒介文本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依赖伴随文本的参与。有了“全文本”的概念,作者最后说出了他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普遍隐含作者。隐含作者的说法来自小说叙述学的研究,但随着各类媒介叙述文本增多,亟需一个更加普遍的概念去概括隐含作者的问题。
无论对于什么体裁的叙述文本,确定文本的范围是寻找隐含作者的关键一步。因各类叙述文本对于伴随文本的“整合能力”有所差异,因此要寻求普遍的隐含作者,必须从“全文本”中推演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各体裁叙述文本的差异性,归纳出普遍隐含作者。回溯到起点,对于广义叙述学中普遍隐含作者的讨论离不开符号学伴随文本的研究。饶广祥在《叙述学如何实现全域敞开》一文中指出,多媒介对于叙述学的发展带来了三大挑战:大量纪实文本的出现,意图性文本呈现泛化趋势,接收者地位明显提升。以往传统的叙述学因为基本没能走出文学叙述的范围,又面临各学科“叙述转向”的现实,不得不做出调整。在此背景之下,《广义叙述学》一书把广告、图像等体裁的叙述文本纳入讨论的范围,为叙述学打破藩篱,敞开全域指明了一条可行之路。符号学被认为是文科中的数学,从人类各种各样的表意活动中抽象出规律,进一步指导表意实践。因此,在叙述学面临“体裁自限”又不得不敞开全域时,运用符号学研究符号文本表意的理论去讨论叙述学中待解决的问题是切实可行的。符号叙述学,必然是覆盖所有叙述文本,得出所有叙述文本普遍规律的广义叙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