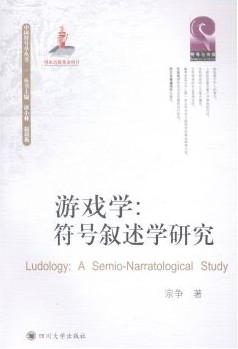作者:
梁旭艳 来源:
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3004 2015-06-30 15:20:53
评宗争《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
(《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梁旭艳
游戏是人类最为古老的一项活动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仍然活跃的、意义深远的人类活动之一。人离不开游戏,缺少游戏的人生是枯燥乏味、没有创造力的。作为不可或缺的人类活动,游戏孕育了人类文明,并形成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但长期以来,对游戏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专业性,仅限于把游戏作为支离破碎的引证材料,这大大降低了对游戏的认知。特别面对蓬勃发展的游戏产业,学界对游戏的研究滞后很多,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看待游戏,给学界研究增添了一抹亮色。
一
20世纪的符号学研究发生了以下新变化:一是游戏自身产生分裂。体育和电子游戏从“游戏”中分离出来。二是缺少对游戏总体的研究。三是多从技术角度研究游戏,忽视了游戏对人的影响。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以此为研究契机,尝试弥合这种分裂和不足,重新以“游戏总体”为研究对象。因而,作者引入了符号学理论,在更宽广的理论层面做整体的研究。本书的几个亮点体现在:一是确立了游戏的定义;二是构建了游戏研究的框架;三是廓清了游戏的内涵和外延;四是进行了消费社会下的游戏文化批判。
给游戏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从古至今,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给游戏一个定义,纷繁复杂,莫衷一是。连维特根斯坦都坦言,给游戏一个定义是不可能的,只能称其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一个整体。本书作者宗争爬梳整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加上自己深刻独到的见解,最后给游戏定义为:游戏是受规则制约、拥有不确定性结局、具有竞争性、虚拟作假的人类活动。定义抓住了游戏最根本的几点特征,对之后的研究肯定会产生不小的启发。
二
构建了游戏研究的框架,游戏文本和游戏内文本。游戏文本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它是游戏设计者——玩者——观者的互动结构。传统的理论结构已经无法解释,只能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框架。作者引入了游戏文本和内文本,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游戏内文本是面向玩者的,游戏文本是面向观者的。
三
对游戏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内涵”和“外延”是符号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书中,作者根据符号的定义划定了边界,据此指出了游戏与其它活动的关联和区别。书中对“扫兴的人”的关注,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和创新。通过对这些游走于游戏与现实之间,不具有所谓“游戏精神”的人的分析,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游戏的五个方面:规则性、竞争性、可能性、虚拟性和交互性。由此也可见出,玩者与游戏的关系并不总是二元对立的,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竞争之外,还有更多的体验。
四
书中的第七章、第八章讨论到游戏的叙述问题,非常清晰的、立体互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讨论了游戏的叙述问题,是本书另外的一个精彩处。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近来,叙述学的研究对象已从记录性叙述文本向演示性叙述文本转化,游戏的叙述问题也多关注电子游戏。本书引入了叙述学理论,视野开阔,不局限于电子游戏,而是纵览全部游戏的。根据赵毅衡先生对“叙述文本”下的定义:有人物参与的变化,形成情节,被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据此定义,游戏文本还是游戏内文本都构成叙述。作为演示性叙述的一种,游戏以其双重互动性与戏剧、电影等形式形成对照。游戏的叙述文本至少存在两个叙述分层:主叙述层和次序数层。主叙述层的叙述者在逻辑上存在,但在叙述文本中隐身。“主叙述者”会在“次叙述层”寻找一个代理者,在游戏中以指令的方式出现,以第二人称的口吻向受述者说话。游戏中的玩者互动,在“次叙述层”形成叙述文本,所有玩家都身兼“次叙述者+次受述者”两个身份。观者既是“次叙述层”的“受述者”,也是“主叙述层”的受述者。
五
对消费社会下的游戏文化进行了批判。“沉迷游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受到媒体和各个领域学者的关注。符号学视野的游戏研究不从心理入手,而是从游戏自身的符号构成和参与者的符号身份两方面入手,解读“沉迷游戏”这一现象,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人们在游戏中流连忘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游戏给予参与者以特殊的体验,并在体验中获得了成就自我的快感,玩者在游戏中所持有的身份,是最靠近自我的身份即是:游戏身份最稳定;认同感最强;身份容量很大。但又指出游戏身份存在的危险性,因为它随时可能遭遇破解和拆穿。由此,对玩者来讲,他或她必须清楚认识到,在游戏互动中产生的表意幻景不可能移植到现实社会,一旦退出游戏,这一意义链条就断裂了。唯如此才能尽量避免产生精神分裂。
最后仍沿用本书作者宗争引用的赫伊津哈的话做结,勉励那些在游戏研究中孜孜以求的学人:
“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游戏成分,因为文明先天地蕴有自身的局限和能力,这种能力不应把自身的发展趋势与最终极的、最高的目标相混淆,它应认识到自身是处于某种公认的界限之内。在某种意义上,文明总是依据确定的规则游戏,而真正的文明正是需要公平游戏。……真正的游戏不是宣传,它的目的在它自身之中,它那平易的精神是幸福的真谛。